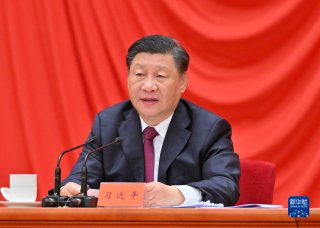融民情于国法:民初法政人对本土地权习惯的继承与改造(6)
辛亥革命网 2022-05-28 09:07 来源:《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2期 作者:赖骏楠 查看:
在佃权处分方式上,大理院也尽可能遵循现有习惯,认可佃权人的处分自由。1913年“上字140号”判例以笼统方式规定,佃权人“自得自由处分”佃权,“毋庸受地主之干涉”。1915年“上字第252号”、同年“上字第360号”、1918年“上字第983号”判例,以及1917年“统字第628号”解释例,则分别许可了佃权的让与、出典和出租。
大理院对田面权习惯的最大改动,发生在增租和撤佃议题上。在本土习惯中,一田两主建立在定额租基础上。只有在荒地开垦阶段,因收益不稳定,才采用分成租形式。由于田面是一种类似于所有权的“世业”,所以即使田面主欠租,田底主也无权撤佃。田面权之所以成为当时土地投资中的优质资产,正是建立于定额租和不许撤佃的基础上。允许增租和撤佃,将动摇田面权的准所有权属性,使利益天平向田底主倾斜,并损害田面权的市场价值。
大理院认可的增租理由,是经济形势发生变化,主要是土地收益增加。如1915年“上字第501号”判例指出,“日后若因经济状况之变更足认为原约租额太轻,设定人原无妨以该邻近地方为标准向佃权人为增租之请求”。又如1920年“统字第1302号”解释例表示,若佃权人改种其他作物,“致地主所分之利益比较独少,当然可以前后收益为比例请求增给”。此外,1916年“上字第501号”判例还允许旗地地主因地租不敷缴纳已加重的田赋,向佃权人请求增租。
大理院确立的撤佃理由,主要是欠租事实。1913年“上字第140号”判例为田底主提供了相当便利的撤佃条件:只要佃权人一年不足额交租,即可撤佃。1915年“上字第582号”判例对此有所限制:佃权人“屡经催告仍怠于支付佃租者”,地主得令其退佃。1921年“统字第1645号”解释例则为撤佃提供了两种欠租事由:欠租两年及以上,或一年以内故意“颗粒不交”。此外,上一解释例还提供了更为宽泛和模糊的其他撤佃条件:“永佃权人虽不欠租,然地主实欲自种,或因其他必要情形,亦许收地。”
在法理层面上,大理院对允许增租和撤佃的解释,依赖的是情势变更原则:“唯当事人间订立此种契约,往往以经济上通常状况为决定意思之基础,而事后发生之特别情形则有非所预期者,自应本于解释当事人意思之法则,以适合于公安公益为条理而予以适当之判断”。因此,即使当事人曾事先约定不得增租夺佃,“如系有法律上正当理由”,则仍可承认一方有解约或增租之权。
但在国家治理层面,大理院其实是在延续清代以来各级政权不断介入一田两主制的长期趋势。鉴于一田两主下的欠租纠纷,常转变为田底主与官府间的抗税纠纷,清代国家长期对该习惯持敌视态度,并试图以禁止或限制田面权的方式,来实现平息纠纷、确保税收的效果。20世纪近代国家建设的资金需求,迫使清末和民国政府提升税率。这导致定额租制下的田底主利益受损,为弥补损失,田底主自然向田面主请求增租,田面主亦自然拒绝该请求。无权撤佃的田底主,当然也无法通过换佃来增加地租,以缴纳新增田赋。显然这一局面既对田底主不利,又对国家收入构成威胁。认可增租请求权和撤佃权,此时就成为调整国家、田底主、田面主间利益关系的制度工具,以期实现确保财税收入、并顺带维护田底主利益的效果。田面主则成为这场博弈中的受损方。
不过,民初的田面主并非一无所获。相反,田面权在此时期获得了大理院在力所能及范围内的充分尊重。它的物权属性、习惯上成立方式、期限的永久性和自由处分空间,都得到大理院判解例正面和全面的继承(这种待遇在清代国家法中是难以想象的)。田面主在增租和撤佃方面的确实遭遇了损失,但这是近代国家建设不得不伴随的代价。
(三)大理院与欧陆物权理论的本土化:向现实低头的“物权契约”
物权行为理论,是19世纪德意志民法科学的重大成就之一。其内容大致为:债权取得方式与物权取得方式应有所区分;债权之取得,依赖债权行为,而物权之取得,依赖物权行为;欲使物之所有权以买卖方式转移,既需要存在债权契约,使出卖人负有移转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之给付义务,又须存在物权契约,即交易双方以“物权合意”和公示(交付或登记)相结合的方式,使所有权真正发生移转(即独立性原则);物权契约之效力不依赖于债权契约之效力,即使债权契约存在效力瑕疵,只要物权契约满足自身的生效要件,就能发生所有权转移之效果(即无因性原则)。尽管该理论能起到保护交易安全这一现实效果,但它更大的优势在于其强大的体系性与逻辑性。对于普遍以德、日为师的民初上层法律人而言,该理论也有着巨大的诱惑力。
大理院推事们在判例中使用了物权契约概念。在1913年“上字第8号”判例中,大理院首度提及该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以直接发生物权上之变动为目的”的契约。物权契约的成立要件,被大理院界定为:(1)当事人须具有行为能力,且须就标的物有完全处分权;(2)标的物须确定;(3)意思表示不违背一般法律行为及契约之原则。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原则也得到澄清:“若卖他人所有之物或不确定之物,则其债权契约虽属有效,然不能即发生移转物权之效力,有时仍不能不为物权契约之意思表示。”上述定义和要件列举,呈现出大理院最初在全盘移植物权行为理论上的雄心壮志。
然而,大理院的上述构想与本土交易方式相去甚远。在习惯中,不存在债权契约与物权契约之分。地权交易通常只需权利让渡人出具一份由自己签押的契据,即发生地权变动之效力。无论是对交易双方还是对中人来说,要在观念上相信土地交易中存在两个独立的契约,尤其物权契约可能仅是一种不具外在载体的合意,是极为困难的。在这种局面下,物权契约的无因性更是无从谈起。此外,由于不动产登记制度的不完善,原版理论中以登记作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生效要件的要求,也是不易实现的。
大理院很快接受现实。尽管推事们在随后的判例中仍使用物权契约一语,但其实质意涵和法律效果都已发生根本改变。大理院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物权契约究竟存在于何处?如果依理论原意,物权合意无须采取任何固定的外在形式。但这种过于抽象的建构,无疑不适合基层审判人员和当事人的理解和执行。为将物权契约“物质化”,1916年“上字第208号”判例径将田房买卖时出卖人出具的地契视作物权契约。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此时债权契约身在何处?由于大理院未就此提供解答,我们只能推测大理院应是认为在同一契据上既包含债权契约又包含有物权契约内容。这种对习惯的妥协,实际上意味着物权契约独立性和无因性前提均遭推翻。在1918年“上字第145号”和1921年“上字第26号”判例中,大理院还承认,原业主在老契上批明转移所有权于他人,也是物权契约的一种形式。这当然也是对习惯的退让。
大理院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是,物权契约要如何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在该问题上,大理院的答案也完全倒向习惯。依据正版理论,在物权合意之外,尚须通过登记这一行为,才能产生物权变动效力。大理院于1916年“上字第149号”判例指出:“按现行法上尚无登记制度,故不动产之物权关系自当以契据为重要之凭据。”物权变动能否对抗第三人,“则应视其契据有无瑕疵”。1916年“上字第208号”判例则更明确表示:“故合法做成契据一经交付之后,其标的物之所有权即移转于让受人。”大理院也多次否认缴纳契税或田赋过户能成为断定物权移转的标准,其理由也正是一经成立契据,物权变动即已发生,而投税和过割只是物权变动后产生的公法上义务。
即使在《不动产登记条例》(1922)颁布后一段时期内,大理院对登记在物权变动上的效力也采取了最为保守的看法。1925年“统字第1948号”解释例在处理重复买卖问题时,仍认为出卖人与第一买受人一旦立契,所有权即发生转移,且能对抗第三人;即使第二买受人将其与出卖人间买卖契约予以登记,该登记亦属无效,并须涂销。大理院的态度显然背离了条例采取的登记对抗主义立场。直到1926年,最新判例才依据该条例,承认了不动产登记的对抗效力。但由于全国大部分地区均未普及不动产登记制度,所以该判例的适用空间无疑极为有限。
在经过反复试验之后,大理院判解例确立的物权变动制度,相比大陆法系的制度模板,已面目全非。大理院版的物权契约不符合德国法的做法。因为德国法上物权契约可以是一个去形式化的、抽象的合意,而大理院要求该契约必须是书面形式。德国法上不动产物权契约要产生物权变动效力,还须履行登记手续,而大理院面对登记制度尚不完备这一国情,长期忽视这一要求。大理院的模式也不是来自法国法或日本法。虽然在法、日两国,只要契约成立物权即发生变动,但只有在登记后该变动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而大理院则主张,一旦契约成立,无须登记即可直接产生完整的对世物权效力。大理院创制的不动产物权变动体系,实际上是对弱国家干预背景下、以私人契据为权利载体的本土地权秩序的妥协和默认。
结语
民初法政人对本土地权习惯之继承和改造事业留给后人的最大启示,是其中蕴含的实践法理:现实经验是高度复杂的,且具有强大生命力,任何单维的意识形态或理论都无法对现实做到全面解释和塑造;面对复杂现实,理应以不同的价值诉求和行动策略予以分别应对;即使这些价值和策略看似在学理中不能兼容,但也能够在实践中协调。在近代法制变革中,捍卫主权、西法东渐、社会治理、国家建设、经济发展、尊重民情,都是法政界不得不在实践中兼顾的任务。
在本土地权习惯议题上,民初法政人在顺应近代法律潮流的基础上,对习惯予以充分肯定。诸多本土地权被纳入近代物权体系中。对习惯的多数改造,也并非简单粗暴的全盘变动,而是出于具有合理性的法理、国家建设和社会治理需求等原因而展开的局部调整。在这一进程中,垦户、长期佃户和典权人先买权得到保障,不利于经济流通的亲邻先买权被废除;田面权的大部分内容以佃权的名义继续存在,但大理院出于国家治理的迫切需求,在增租和撤佃事宜上做出对田面主不利的规定;典权得到立法者的高度重视,但他们也担心永久回赎权会产生不利经济后果,所以对回赎期限进行限制;本土抵押权的高度流通性得到承认,抵押权实行方式也做到了新旧兼容,但对债务人明显不利的流押被坚决禁止;源自德国的物权行为理论,也在实践中被彻底本土化。除了较为复杂的对典权的改造情形,上述变革基本都具有近代语境下的历史正当性。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2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