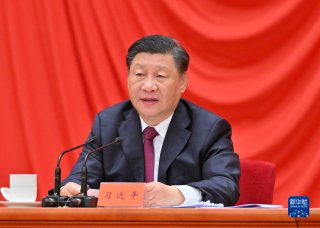融民情于国法:民初法政人对本土地权习惯的继承与改造(3)
辛亥革命网 2022-05-28 09:07 来源:《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2期 作者:赖骏楠 查看:
(二)实践逻辑与对本土地权的重新重视
抱有这些观点的人并非仅活在意识形态和抽象理论之中,他们也是身处现实世界中的、活生生的人。鉴于当时学术界与实务界间的紧密联系,民初法律界作为一个整体,是法律体系运行的直接观察者和亲身参与者。即使是位于司法体系最高层的大理院推事们,也在该院运行的15年间(1912-1927)审理了16000余起民事上诉案件(其中物权案件近4000起),并就民事疑难问题提供了300余条解释例。他们在深入接触审判实践之后,自然能体会到外来规则与本土习惯间的持续扞格问题,也就自然会反思本土习惯的近代意义、习惯与法律的协调等问题。
这种反思首先体现在对《大清民律草案》中某些不合国情之物权种类的批判上。如土地债务制度就受到激烈抨击。有论者指出:“查土地债务观念,原为我国社会所无,民草袭取他国成规,投无疾之药,既背国情。故事实上此章规定,直同空文……其结果民法规定与民间经济生活,不相协调,殊为一国法典之玷,非仅形同赘疣已也。”该草案袭取自日本永小作权的永佃权制度,也受到同一作者批评:“我民草不顾法理,不察国情,袭取他国不当成规,抹煞一切,吾人实未敢苟同。”
对习惯议题的反思,还体现在主张将部分地权习惯纳入民法典的声音之中。相当数量的法律界人士主张保留典权。其核心理由,便是典习俗的持久性与普遍性:“此种物权,沿用既久,人民之信仰已深。根深源远,弥漫全国,无废除之理由,有采取之价值。”曾任大理院推事、庭长和朝阳大学兼职教授的朱学曾,在其物权法讲义中,虽基本依赖《大清民律草案》所规定的物权体系进行讲授,却在讲义最后以附录形式专门介绍典权制度。也有论者主张应保留一田两主习惯,并否认有关该习惯不利于土地改良的看法:“佃户有田面权,则对于土地有切己之利害关系,春耕夏耘,必尽其力,箕裘克绍,视同己产,是与〔于〕业主亦未尝无益。”
有论者从更根本的制度设计角度,主张突破严格的物权法定原则,通过在民法典中明文规定的方式,对不同于法典规定的特殊物权习惯予以优先适用。该作者认为,习惯未必有碍交易安全。只要略加调查,各地习惯之内容便可掌握。在这方面,商事习惯的适用已做出榜样,“且如商事性质,较物权习惯复杂数倍,而法律无规定时,借用商习惯办理,不闻有阻碍商业之说,是可未因噎废食也”。尊重习惯也未必会阻碍收回领事裁判权:“外人之不肯改正条约者,谓吾国法律之不善,非谓吾国法律之不同,各国法律,均与本国历史互相关系,何尝尽出一辙?”
可见,一种“实践逻辑”,或者说“矛盾性共存”的逻辑,出现在民初法律界有关地权习惯的思考中。从意识形态和学理上主张严格限制习惯,但又从实践出发意识到必须尊重习惯,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却经常发生在同一批人甚至同一个人身上。尽管他们认为必须牺牲习惯以迎合列强,主张制定法至上的法源理论,崇拜绝对所有权和物权法定主义,但在实践的冲击下,不得不严肃对待习惯。该时期法学界对欧陆理论的研究由于多处在消化吸收阶段,所以尚难以在学理上将这些理论与中国实践相融合。但他们至少愿意在实践中将这些冲突的要素调和,并勇于将其表达。
三、 民初立法实践对本土地权习惯的继承与改造
(一)有关本土地权的立法概览
从数量和规模上看,民初政权在民事立法上成就相对有限。这一方面是由于承担立法职能的国会在动荡政局下难以维持正常运转,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法政界自身对速成式法典编纂的克制。不过,在该时期有限的地权立法中,我们仍可看到,对欧陆法理和立法例的依赖、对本土习惯的重视、社会治理与财政国家的急切需求,以复杂方式交织一起。
由于《大清民律草案》始终未能生效,该时期在名义上充当民事一般法的,是《〈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民国建立后,为解决各审判机关在民事案件中“无法可依”问题,参议院、大理院先后将《大清现行刑律》(1910)中的“民事有效部分”确认为法源,要求各审判机关适用。在地权问题上,该法律基本继承了《大清律例》中“盗卖田宅律”“典买田宅律”“盗耕种官民田”及相应条例中的简略条文,主要涉及田房产权保护、典与绝卖的区分标准,及典交易中回赎、找贴、别卖等方面规定。很显然,这寥寥数条规定不是对本土地权秩序的完整呈现,难以胜任日常案件中的法源角色。
作为民初法律界在制定民事一般法方面的重要尝试,1926年完成的北京政府《民律草案》(以下或称《民国民律草案》),尽管仍遵循欧陆物权法的体例,但已对本土习惯做出某些实质让步。该草案系在《大清民律草案》的基础上修订而来,但修订人员全为本国专家。在地权议题上,相比清末旧草案,新草案的最重大变化,一是删除了备受抨击的土地债务制度,二是增加了作为独立物权的典权(第998条至第1014条,相关讨论见下文)。此外,永佃权一章也吸取了部分学界意见,明文承认某些有关减租、撤佃之“特别习惯”的优先效力(第870、872条)。在其他不动产物权方面,新草案较之《大清民律草案》并无本质变化,甚至保留了不动产质。
在上述一般法及草案之外,民初政府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地权的特别法令。因为这些法令是由政府行政部门(或司法行政部门)主导制定,所以其内容常带有特定部门的利益考量(如减轻诉讼负担、便利征税),从而可能呈现出对本土地权秩序较为简单、僵硬的干涉。即便如此,部分法令仍对习惯做出重大让步。且由于这些立法多采取相对灵活、具体的政府法令形式,所以它们既满足了民初国家在社会治理中的种种迫切需求,又尽可能避免了在过大范围上对习惯及其支撑的固有社会经济秩序造成干扰。
最能体现政府财税利益考量的,是由财政部主导出台的《契税条例》(1914)、《验契条例》(1914)及《奉天永佃地亩规则》(1918)等法令。前两部法令系同一日(1914年3月12日)出台,其宗旨在于延续清末新政已开启的契税整顿运动,以便进一步改变当时普遍存在的白契不税、短价匿税等问题。《契税条例》规定,自该条例施行之日起,对逾期缴税和匿报契价等行为,予以严惩(罚金最高可达漏缴税额之16倍,政府甚至有权低价征收涉案不动产)。该条例施行前所有未缴税之不动产交易,也须在6个月内补缴税款,否则同样严惩。为配合《契税条例》的实施,《验契条例》要求民间所有不动产典、卖契纸均赴官呈验,以确保所有白契补缴契税。
在民初民事立法中,《奉天永佃地亩规则》可能是政府部门在财政考量驱动下急功近利、罔顾习惯与民情之最典型产物。该法令由奉天省政府制定,并由北京政府财政部联合内务、司法两部呈准大总统施行。为确保辛亥以来该地不断增长之田赋的足额征收,该法令在《大清民律草案》本就不利于永佃权人之规定的基础上,对永佃权人予以更脱离习惯、变本加厉的限制,甚至对其施以本应由业主承担的田赋负担。永佃权的期限被限制在50年以下,从而失去了真正的永佃性质。佃户转佃须经业主同意(《大清民律草案》无此要求)。即使遭遇天灾事变,佃户也无权请求减免地租。只要佃户一年全不交租或不足额交租至两年及以上,地主就有权撤佃(比《大清民律草案》更严苛)。田赋原则上“由佃户负担代纳”;若双方约定由业主完纳,则业主有权增租(即使本已明文约定“永不增租”)。业主在转移永佃地所有权时,也有权同时撤佃,且只需支付少量补偿。所幸该法令只施行于奉天省,否则必将引起大范围的民情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