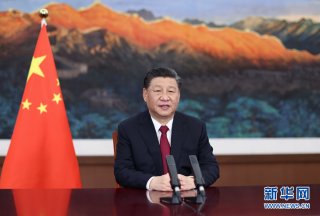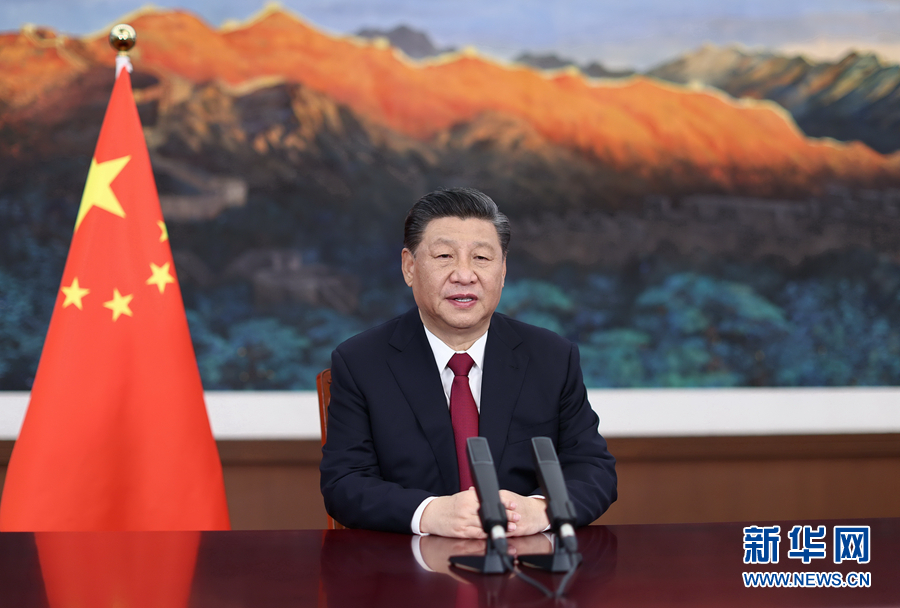冯天瑜的文化史研究之旅(6)
辛亥革命网 2021-04-15 09:34 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周积明 查看:
冯天瑜的《“封建”考论》不仅学术精湛,视野宏阔,而且充满强烈的现实意义。五四以降,“封建”概念的异化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涉及到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以及对中国革命的任务和革命对象的判断。从这一意义而言,《“封建”考论》“已经超出了对一个概念演变的考察,超出了中西日互动的讨论框架”[27](P147),“原来在泛化封建观的‘范式’下所得出的一些结论可能被推翻,一部中国历史的宏大叙事或将重新书写”[30](P116)。由此注定了完成这部著作不仅需要敏锐的学术眼光,而且需要巨大的理论勇气。早在1993年李慎之初读《中华文化史》中关于“封建制度”考辩的论述后,就曾致信冯天瑜,指出“滥用‘封建’这个词原来正是政治势力压倒‘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的结果。因为时下所说的‘封建’以及由此而派生的‘封建迷信’、‘封建落后’、‘封建反动’、‘封建顽固’……等等并不合乎中国历史上‘封建’的本义,不合乎从Feudal、Feudalism这样的西文字翻译过来的‘封建主义’的本义,也不合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封建主义’的本义,它完全是中国近代政治中为宣传方便而无限扩大使用的一个政治术语”[31](P208-209)。正因为如此,《“封建”考论》出版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回响。2007年10月,北京史学界召开“封建名实问题与马列主义封建观”论坛;2008年10月,武汉大学召开“封建社会再认识”的讨论会;2008年12月,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召开“封建与封建社会问题讨论”。刘志琴评论说:“一本著作连续三年分别在中国的南部、北部和中部地区的文化中心地带进行连续讨论,在史学界是少有的现象,这事实本身就说明其影响力非同一般。”[27](P45)在这场意义深远的大讨论中,虽然有学者试图把关于“封建”名实问题的探究政治化,称该书有三大罪:一是“反马克思主义”,二是“否定中国民主革命”,三是“否定了中国现代史学成就”[26](P3)。谓“马克思主义史学恐怕要地震了。这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来说,当然是严重的指责和挑战”[29](P24)。但更多的学者高度评价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与意义。张绪山评价说:“冯氏此著是我国学术界‘封建’概念研究的界碑。”[27](P159)方维规赞誉说:“此书当为史学不同凡响之作”,“在汉语历史语义学领域,《考论》的重要性及其典范意义是毫无疑问的”[27](P148)。
五、义理、考据、词章、经济的互济
1988年,冯天瑜在《中国文化史断想》的序言中曾自叙:“笔者自七十年代末便决心竭尽绵薄于中国文化史。”[4](PII)40年过去了,冯天瑜践行了他的初衷。侯外庐曾寄望于冯天瑜能走出“文革”噩梦,“成就一个真正学者的事业,为这个民族做出自己的贡献”(陈寒鸣转述黄宣明回忆)。冯天瑜不负侯老所望,在中国文化史研究领域创造了显赫的业绩。从《上古神话纵横谈》到《中华文化史》《中华文化生成史》以及《“封建”考论》,每部著作都映现出智者光芒与通博气象,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文化史大家。
有容乃大、渊源有自。冯天瑜的父亲冯永轩(1897-1979)1923年入读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前身),师从文字学家黄侃(1886-1935)。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全称“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创办,永轩先生考取为一期生,受业国学家梁启超(1873-1929)、王国维(1877-1927)、语言学家赵元任(1892-1982),其毕业论文《匈奴史》指导教师就是王国维。在武汉大学和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培育下,永轩先生专于古文字学、西北史地与楚史,学养深厚,博闻强记,于经传及其诸家注释背诵无遗。冯天瑜自幼便得永轩先生开庭训讲堂,耳提面命,精读先秦诸典与太史公书。复因母亲在湖北省图书馆工作,得天独厚,长期流连于馆藏,浸润于中外文化名著中,由此打下深厚的学术根柢。更重要的是,在冯天瑜身上,承传了从黄侃、梁启超、王国维到冯永轩的内在学脉。这种承传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代有突破:永轩先生突破了章黄学派词章之学的传统,把王国维和梁启超的学问结合起来。冯天瑜则近承永轩先生学术,远绍梁启超、王国维,由此铸就了他的大视野、大学问以及悠游于义理、考据、词章、经济互济空间的学术气象。
义理一词,最初指合于一定伦理道德的行事准则。其后衍绎为儒家经义。宋明理学兴起后,“义理”一词被广泛使用,多用来指思想或意旨。台湾中兴大学胡楚生教授在《方东树〈汉学商兑〉书后》中概言说:“义理之名,为思想、义趣、理念、意旨之总称。”[32](P255)冯天瑜初入学术门墙,即深感理论思维紧要。为此广读思想史名著,“学习以往的哲学”,其中对冯天瑜影响最大、被他视为“看家书”的有三本,一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二是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三是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黑格尔《历史哲学》“把历史视作世界性辩证过程的思想”;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洞察在历史发展中有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力量,这便是“一动而不可止”的“势”;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以仅十万言的篇幅把中国古典的政治学说推向高峰,在若干方面可以与孟德斯鸠、卢梭的思想相比肩。这些先哲的睿智给冯天瑜巨大的思想启迪和思维营养。除三本看家书外,冯天瑜对于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如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都非常熟悉,对中国古代的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他更是熟稔于心。中外古今的理论沉淀在冯天瑜的思想和学问之中,使他对问题的看法、对问题的分析,往往高人一筹,凡读他的文章和著作,一定会被渗透于文字中的理论色彩所吸引,得到思想上的启发。
“考据者,考历代之名物、象数、典章、制度,实而有据者也。”[33](P152)中国古代考证之学自东汉郑玄始绳绳不绝,至清代乾嘉时期臻于高潮,成为中国学术中十分重要的传统。冯天瑜对考据殊为重视,认为:“对一切以学术为鹄的人来说,都有占有材料,进而对材料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必要。”因此,辨析材料决非考据家的专利,而是全体学者的必修功课。“对于史学工作者而言,既以‘实录’为治史目标,也就格外需要相当的考据功力。”[34](P34)但是,冯天瑜虽然重视考据功夫,“钦佩乾嘉学者的渊博和谨严”,却又不愿追其故迹,将生命全然消耗在名物训诂和一字一句的疏证上[34](P34)。他的《“封建”考论》就深得宏大而不离考证的要旨,全书从“微小”的“封建”切入,在材料的搜集上上下求索,“竭泽而渔”,关键资料几无遗漏,“将近百年中国政治和学术密切关联的问题,有条不紊地完整地勾画出来”[27](P158)。
“词章”一词有二义,一是诗词文章的总称;二是指文章的修辞与写作技巧。所谓讲究辞章,就是追求能更好传递文章内容的完美的表述形式。冯天瑜十分注重词章。他说,“我甚钦仰前辈史家的文质彬彬,不满旧八股的呆板乏味,虽自叹才情欠缺,却心慕手追,力图文章有所长进。叙事纪实,务求清顺流畅,娓娓道来;辩驳说理,则讲究逻辑层次,条分缕析”,“除史论以外的历史著作,哲理最好深蕴于叙事背后,主题更应贮藏于事实展现和形象描绘之中”[34](P34)。由于冯天瑜广为涉猎文史哲、美学、宗教学、政治学、经济学、地理学、神话学、生物学,“多识乎草木神兽之名”,在写作时博采古今中西,俯拾各类知识,因此,他的论著往往在一个阔大的场域中纵横驰骋、酣畅淋漓、清通流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苏轼语),故有一种博通的大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