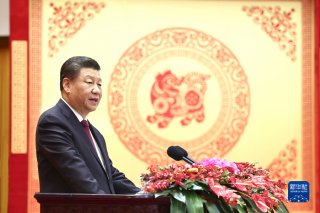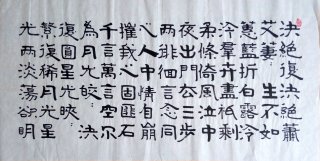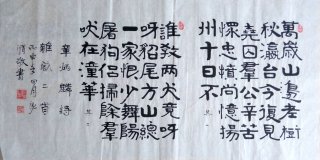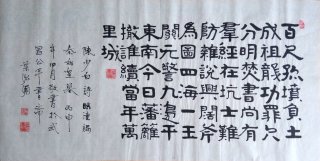“革命军北伐,司法官南伐”——1927年前后的政权鼎革与司法人事延续(4)
辛亥革命网 2022-02-12 08:42 来源:《近代史研究》 作者:李在全 查看:
在南京政府司法官员选任规则中,曾任司法官者即具有任用资格,加上要员引荐推介,北京政府司法人员便可“名正言顺”地进入南京政府司法系统中。北京政府被推翻后,余绍宋南归杭州,因其书画颇具声名,以鬻卖书画为生,生活无忧,故未加入国民党政权。但因余绍宋在法律界深厚的人脉关系,故不断有人找他推介求职。据余氏日记记载:1928年9月14日,“近日法院将增设县法院数处,诸人纷来求荐书,可厌亦可怜也”;10月18日,致函浙江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郑文礼,保荐熟人充任检察官;次日,很多人来请余氏向王宠惠、殷汝熊推荐求职。这让余绍宋深感难以应付,他在日记中感慨:王、殷“两人在位,余终不免被扰,原来落伍人识得阔人亦不是好事,无怪古人云‘入山入林惟恐不深不密也’”。1929年6月29日,又有许多人请求余氏推荐法院职位,“近日浙省又须增设县法院,余又将受累矣”;8月13日,郑文礼来访,余绍宋推荐三人担任法官;9月23日,余绍宋致函殷汝熊,推荐6人担任法官,他在日记中感叹:“添设法院于我何与,而时被诸求者围困,可怜亦可恨也。”
1931年底,罗文干出任司法行政部部长,郑天锡任次长。在北京政府时期,罗、郑均是余绍宋关系密切的僚友,因此,找余氏推荐谋职者更多。1932年1月,余绍宋在日记中记述,“因罗钧任(罗文干)为司法部长、茀庭(郑天锡)为次长,冀有所干求者,人多不具记”;数日后,余氏再次感慨:“茀庭作官,余将不胜其累矣。”以上,均是余绍宋以国民党体制之外人士的身份,向体制内的熟识友朋推介人员;与此同时,已在国民党体制内任职的友人则欲把余绍宋拉进体制内。1932年1月20日,余绍宋收到郑天锡来信,“拟聘余为南京法官训练班教务主任”,22日余回函谢绝;7月25日,余绍宋收到原法曹僚友何枚如来信,曰:罗文干部长拟任命余绍宋为司法行政部视察员,“视察各省区司法”,次日余回函何氏,请其转告罗部长,“余不能为彼之视察员”,转而推荐他人;9月27日,余绍宋收到曾任北京政府江苏、湖南、浙江等省高等审检厅长官,现任安徽高等法院院长的陈福民来函,责备余绍宋“何故不出山”,谓罗文干部长“相招再三再四,余俱不应,实非人情”,余回函陈说,不少僚友已出山任职,自己则坚持不出山。从上述所载余绍宋不断被人请托求职,乃至罗文干、郑天锡再三邀请余氏出山任事,均可见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司法系统之一脉相承。
不独余绍宋如此,很多原北京政府官员都有类似经历。多次出任北京政府司法总长、政学系首领之一的法律名人张耀曾,1928年12月由北平抵上海。1929年1月14日,张耀曾与王宠惠晤面,张向王推荐原先僚属何基鸿、沈家彝、熊兆周;16日,原北京政府江苏审判厅推事沈沅来到上海,请求张耀曾向王宠惠“说项”,张允诺写信推荐,同日,张耀曾致函何基鸿,告知其与王宠惠“所谈情形”;22日,为何基鸿、沈沅谋职之事,张耀曾致函王宠惠,予以力荐。这些人员后来都进入国民政府任职,如沈家彝,1930年5月任司法行政部参事,罗文干任部长时,1932年5月沈氏调任上海第二特区高等法院院长,1936年又调任河北高等法院院长。
北京政府的司法系统人员几乎原封不动地进入南京政府中,因此,南京政府司法部门的人脉交游、司法风格、政治文化明显地延续着北京政府时代风气。身在上海的张耀曾、沈锡庆在他们的日记中,记载着这些人脉交游的信息。1929年4月17日,原北京政府司法官员梁仁杰拜访张耀曾,告知他将赴江西任高等高院首席检察官;1932年3月12日,梁仁杰、沈家彝拜访张耀曾,言原北京政府司法总长董康将赴南京法官训练所任职。1932年1月出任上海地方法院院长的沈锡庆,几乎完全生活在原来的人脉网络之中:3月26日,沈锡庆参加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首席检察官王振南的宴饮,同席参加者有第二分院院长沈家彝,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院长周先觉,高分院庭长郁华、钱鸿业,地院庭长周翰、首席检察官汪祖泽等,无一不是来自北京政府的司法人员;4月23日,上海地方法院新任书记官王道周到院就职,王系沈之旧属;11月9日,第一特区地方法院新任院长郭云观拜访沈锡庆,郭氏曾任北京政府大理院推事,此次系由司法行政部参事调任而来;17日,上海地方法院新任首席检察官楼玉书来拜访沈锡庆,楼氏系从江宁地方法院调任而来,也是“二十余年之老法官也”;1933年1月13日,沈锡庆赴镇江地方法院,拜访院长、庭长和推检人员,发现“内有半数系予旧属”;29日沈锡庆分别拜访“许世英、章宗祥、董康、张耀曾、薛笃弼诸总长,并与章、张两总长长谈”,口口声声“总长”,是已经被推翻的前政权之司法总长。可见,虽已是南京政府司法官员,沈锡庆依然生活于北京政府人际网络和政治文化之中。
中国现代法制改革肇始于清末新政时期,移植西方“司法独立”“司法不党”理念与制度,司法官员不卷入政党政治与政争,规定推检人员不得为政党党员或政社社员,他们一般都严守证据、程序规则,坐堂审案,思想较为保守。从清末到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经过二十多年时间,这些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根深蒂固,已成惯习。这些北京政府司法官员未经“革命洗礼”,大量进入国民党政权,自然也将这些理念和方式带入南京政府中。国民党标榜“以党治国”,坚持一党专政,司法系统要掌控在国民党之手,推行司法党化,这些来自北京政府的司法官员,对此并不了解,亦未必赞同。对此持反对意见者,比比皆是,如罗文干、董康、郑天锡、石志泉、夏勤、赵琛等人,他们认为司法党化将会破坏司法的独立,难以维护法律的尊严;在他们看来,执政党的主要任务和责任是制定有关国家内政、外交等方面的重大方针政策,司法是带有职业性的专业工作,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不是一般从事党务工作的人员可以胜任的。这种讲求法律专业属性、强调“司法不党”之理念,存在很多法律人士脑中,张耀曾就对王宠惠说:“法官宜多用熟手,普通民刑审判,不用着党的色彩”。余绍宋也致函司法行政部次长郑天锡,建言“法官入党,流弊太大,宜禁”。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根据政治斗争需要,在“革命”者审判“反革命”者的旗号下,在普通法院之外广设特种刑事法庭,主要是审判共产党员与政治异议人士。这对国家司法正常运转破坏很大,也遭到国民党高层一些人士的反对。1928年8月在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国民党元老、此时兼代司法部长的蔡元培提议废止《特种刑事临时法庭组织条例》,所有反革命及土豪劣绅案件均归普通司法机关审理,提案获准通过。如此一来,大量政治性案件转入普通法院审理。
从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角度而言,司法系统必须配合国民党政治斗争的需要,然而,来自北京政府的司法人员显然无法做到这点。他们审案时“往往死抠法律条文,司法审判程序迂缓繁复”,由这些人员组成的司法机关无法成为国民党运用自如的政治工具。因此,很多党部对法院非常不满,经常发生矛盾。1929年4月,天津特别市党部向国民党中央报告:“该市前曾组织惩共委员会,惟该机关职权,对于共党,只能逮捕,不能处理,以致被捕共党,移送法院后,往往宣告无罪,益令共党无所忌惮。请赐予惩共委员会以处分共党之权,以便应机处理,或请明令法院,对于审理共党案件,非经党部同意,不得滥予释放”,该报告还称:“各地关于审决共产党徒案,党部对法院,不少同样感想。”国民党中央也承认:近来各地破获共产党案件甚多,“党部对于法院仍虑其偏重证据,轻易释放,迭据陈述前来”。掌控中统的国民党要角徐恩曾指斥:“那些司法检察部门都是无用之辈,我们要做的许多重要事情,都得不到他们相应的配合。” 1934年10月,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王子壮观察到,“吾国司法界深闭固拒,于本党政府之下而处处有反党之事实,不一而足”,因为“此司法来自北平,已自成派故也”。王子壮所言南京政府司法系统来自北平,自成系统,而且“处处有反党之事实”,代表了国民党方面人士对这时期司法系统的基本观感。
四、 成因考析
关于1927年前后中国南北政权之间的司法人事问题,一位民国司法人员晚年记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久,因为自身审判人员与水平不足,召回原北京大理院与检察署旧有推检官员,赴南京任职,以充实最高法院与检察署的审检重任,更选调部分北方旧有司法官员充实南方各省法院;各省高等、地方审判厅易名为法院,各级检察厅易名为检察处,只有少数首长更换新人,旧有推事、检察官全部留用,仍任原职,因此,当年曾有“革命军北伐,司法官南伐”之谑语。证诸史实,大体如是。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在两个敌对政权之间,为何会发生这种“革命军北伐、司法官南伐”现象呢?
从清末革命开始,历经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国民党虽几经改组,但其思想纷歧、组织散漫、人员庞杂、党力低下可谓痼疾。因此,1923、1924年孙中山决定“联俄容共”,学习苏俄列宁政党模式改组国民党,试图改组建立一个具有严密组织和强大执行力的国民党。但实际上,所学基本是表面功夫,国民党依旧故我,内部信仰纷乱,人员庞杂,没有根本改变。从理论上讲,国民党对各级行政司法工作人员,要求尽先在党内选用。1927年9月,国民党中央要求:“通行各级政府行政司法机关,所有上级干部人员须尽先在党内选用,非党内确无适当人才时,不得援用党外之人”,然而,实际上很多是“援用党外之人”,而且基本没有严格的政治审查。如此一来,许多国民党外人员,甚至是“反党”人士,都进入国民党政权之中。
随着北伐战争迅速推进,国民党控制地域急剧扩大,管理与建设人才严重不足;在这过程中,国民党内部斗争加剧,外部往往通过与北方势力妥协而换取军事胜利,招降纳叛,大量的北方军阀、官僚、政客借此进入国民党政权中。在1929年南京政府10位部长中,至少有4位是北京政府官僚,因此,当时社会上有“军事北伐,政治南伐”“南京政府,北京内阁”之语。若细化考察,在南京政府初期中央各部的事务官员中,司法行政部几乎全部来自北方,外交、财政、海军、交通等部,北方官僚所占比例也很高,均超过半数。作为国民党领袖,蒋介石是此局面的主要推手与操控者,他也预知其之后果,曰:“今之行政机关所最难者,不用一旧有人员,则手续多有不便;用一旧有人员,则旧有之积习,即随之而入”,似乎是在两难之中,国民党中央只能如此应对。在抗战前夕,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王子壮在日记中写道:“北伐时期极为迅速,于一二年之时间而能奠定全国,此固可喜,然牵就各方,容纳投降之事则甚多,于是,自己之阵营转为复杂”;他认为,国民党政权仅是形式而已,“实质上绝非党的政权”;两月后,王氏又写道:“国府建都南京已达十年,政治上虽有相当之进步,而关于人事制度上之改革迄无成功,良以革命力量扩张太快,缺乏适当人才以应政治上之需要,于是兼容并包,无所不有。北京之官僚力量逐渐南移,复运用其手腕,达到官运亨通之地步。此一辈人多善奉迎,对事敷衍,难期实效。”政治虽有进步,但国民党变得复杂,人事难言成功。
和北方势力妥协,虽然缩短了国民革命的军事进程,南京政府也得到很多具有行政管理专长和经验的北方官员,然而,这给国民党带来的危害也很大。国民党本来即内部不团结,北方官僚大量转入且被委以高位,无异于进一步撕裂国民党,使其更加庞杂。对此,许多较纯粹的国民党人无不愤恨,出身广东的国民党要角马超俊晚年忆述:“奠都南京后,一般官僚政客倡言:‘作天下事,用天下人’,藉谋进身之阶。因此旧日官僚,络绎南下,混入中央政府。”亲身参与北伐之役、后来成为国民党政要的雷啸岑,晚年更是痛心疾首,他说:南京政府成立后,对北洋军阀部队,“招降纳叛,来者不拒,这些旧军头对三民主义毫无认识,士兵们亦缺乏政治训练,只是换插一面青天白日旗,人事经理一仍旧惯,即号称为国民革命军,各军的首领且多加官进爵,位跻封疆大吏,甚至有尚未经过入党手续,竟被选为中央委员者”;与此同时,南京政府各部门成立,“许多职员皆系任用北洋政府的旧官僚”,“这般旧官僚只要填写一张入党表,身穿一袭中山装,就成为风云人物,而以国民党同志自居”。继而,国民党中枢声明:凡属供职国民政府所属机关的人员,一律以党员论,“革命的国民党招纳了这许多不知三民主义为何物的军阀官僚份子,乃对党发生腐蚀作用,党基从此动摇,党纪乃趋堕败,我认为这便是国民党最后在大陆上失败的基本因素”。民国后期的军政焦点,看似国共两党之争,实际上,与共产党相比,国民党并不算一个“党”,而是各种庞杂势力的混合体。
司法领域就是如此。由于国民党自身并无多少班底人马,几乎全部来自北京政府,经由王宠惠、罗文干等人进入国民党高层,在标榜法律专业知识、注重司法实践经验等理念下,在法律职业者内部,相互推介援引,几乎是系统性地进入国民党政权中,故出现“革命军北伐,司法官南伐”现象。这现象的产生,既与晚清以来逐渐形成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有关,也与法律界的“司法不党”理念有关。从世界近代法律史观察,法律专门化、人员职业化是与近代社会分工密切关联的长期历史演进过程,法律职业活动逐渐形成专有的知识或技术,未经专门训练的人无法从业,同时,法律界为追求自我利益并保证法律服务质量而形成行业垄断等。中国现代法制、司法改革肇始于清末新政时期,远师欧陆,近法东洋,在京师、省城和商埠等地渐次筹组新式审检机构,讲求审判的程序化、人员的专业化和职业化。辛亥鼎革后,民国北京政府赓续其事,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形成一定规模的法律职业群体,包含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律学者等,这有利于构建现代法治社会,但同时也产生一个相对独立、自治(或封闭)的法律职业系统。王宠惠、罗文干等即是这个系统的领袖人物。
在强调司法专业化、人员职业化、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理念下,北京政府时期司法官员有一套严格的选拔、任用、升迁、保障制度。在此理念与制度之下,很多司法官员对社会现实,包括政党政治保持相当的距离。有学者对此作了分析,认为当时很多司法人员是保守的,这缘于他们长期深受“司法独立”思想的影响,“司法独立”是18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的“天经地义”,依照西方传统观念,司法独立的一项重要条件是司法官员不卷入政党政治,因此,许多国家都在法律上规定司法官员不得参与政党活动;肇始于清末的中国现代法制、司法变革,以西洋制度为学习对象,把西洋司法独立的引入中国,也规定在职司法人员不得为政党党员或政社社员;经过北京政府时代,到南京政府成立时,这种规定在中国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了,可以说,司法官员不得参加政党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了。因此,不但许多服务司法界的人不愿谈“党”,就是社会上一般关心司法的人也不希望他们与“党”有何关系。无疑,这种“司法不党”理念是造成“革命军北伐、司法官南伐”的原因之一。
若放宽视野,1927年前后南北政权鼎革中的司法人事延续,还有一定的国际原因。鸦片战争后,列强攫取了在华领事裁判权,随着民族危机加剧与国人民族意识觉醒,朝野均深感事态之严重,为此,清政府亦有所努力,清末变法修律即在此背景下展开。辛亥鼎革后,历届民国政府均谋求撤废列强在华领事裁判权。几经斡旋和筹备,旨在撤废领事裁判权的法权会议于1926年初在北京召开,王宠惠、罗文干正是法权会议的中方主事者。会议期间,中方虽然做出诸多努力,但列强在肯定中国法律和司法制度的若干进步后,指出中国法律、司法和监狱制度的诸多弊病,并以此为理,拒绝了中方撤废领事裁判权之要求。按照《调查法权委员会报告书》统计,中国法院和司法官员情况是:各级新式法院139所、法官(包括推事与检察官)1293人,列强认为中国“经训练之法官人数过少”。1927年南北政权鼎革后,南京政府基本承续了北京政府的中外条约体系,这样,撤废领事裁判权的历史任务落到南京政府身上,而且,主持南京政府司法中枢的仍然是王宠惠、罗文干等人。在撤废领事裁判权的外部压力下,南京政府只能在接续北京政府司法系统的基础上继续展开工作,而无法真正另起炉灶。
结语
“革命军北伐、司法官南伐”有利于国民党政权承续北京政府司法基础,实现国家司法运转的平稳过渡,但对国民党来说,也带来很多问题。在王宠惠、罗文干主持下,大量北京政府司法人员进入南京政府中,有国民党员呈控中央政治会议:司法部成为王宠惠等人之“宗祠”,“不用本党忠实党员,而尽易以私人”,司法部200余名职员中“在党籍者不过十人”,故请“另易忠实同志主持司法”;罗文干出长司法行政部,有人向国民党中央呈控,抨击罗氏“专事引用反革命腐劣分子以排斥革命司法人材”,“不应再容其久据最高司法行政机关”。这些或多或少反证了这种人事变动给国民党带来的危害。这些进入国民党政权的司法人员与国民党并无渊源,也未必认同国民党理念与学说,大多数人仍持北京政府时代的“司法独立”“司法不党”理念,遵守证据、程序方面的原则,因此,他们多半不能配合国民党政治斗争,而且“反党”现象频发。正是针对这种状况,在1934年前后,国民党元老居正执掌司法院后,再次高举“司法党化”大旗,努力把司法系统“化”入国民党之中,成为国民党能够运用自如的统治工具。然而,在整个国民党统治时期,囿于各种原因,司法系统始终未能成功地“化”入国民党之中,亦未能成为国民党统治的有力工具。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6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