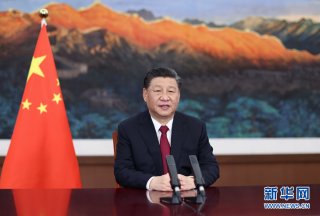人人皆革命党——从“新革命史”谈起
辛亥革命网 2021-05-11 09:27 来源:《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作者:彭剑 查看:
引言
革命曾经是中国近代史领域研究的主题,但是,在20世纪后半段,革命史研究却有退潮之势,出现了“把中国革命从历史舞台中心移开的倾向”。不过,革命毕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问题,将它从历史舞台中心移开,就会使史学研究抓不住要害,造成研究的碎片化。有鉴于此,一批学者或坚守,或投入革命史研究,从而在21世纪之初形成了“一股新的革命史研究热”。正是在此过程中,一个新的学术概念“新革命史”出现了。这一术语虽然不能涵括近些年来所有革命史研究的新现象,但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学界将革命史研究推入新境界的努力。
这一概念是李金铮提出来的。据其自述,2008年,在“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暨纪念乔志强先生诞辰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他提交的论文《何以研究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的最后一节以“向新革命史视角转型”为标题。这篇论文经作者修改充实,成为次年他在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举办的全国社会史研究生暑期学校的讲题《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的社会史视野》。在那之后,又经修改,以《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为题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从那以后,“新革命史”这一术语遂广为人知。即使不以革命史为专攻的学者,对这一术语也“如雷贯耳”。
那么,何为新革命史?李金铮在2016年发表的论文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如果说要给“新革命史”做一个比较明确的界定,大概可以这样表述:“新革命史”是回归朴素的实事求是精神,力图改进传统革命史观的简单思维模式,尝试使用新的理念和方法,对中共革命史进行重新审视,以揭示中共革命的艰难、曲折与复杂性,进而提出一套符合革命史实际的概念和理论。
这一定义令笔者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特别强调新革命史与中共革命史的关联。其后,在2018年和2019年发表的相关论文中,李金铮也作了几乎相同的阐释。但是,如此界定“新革命史”,总令人感觉有所不妥。由于他将“新革命史”仅仅定位为推进中共革命史研究,加上迄今为止冠以“新革命史”标题的研究成果,全都是关于中共革命史的,且大都发表于中共革命史的专业期刊,这就给人留下很深的“新革命史”只是“新中共革命史”的印象。不以中共革命史为专攻的学者可能忍不住问:“传统革命史”关注的对象还包括了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国民革命,“新革命史”却只关注中共革命,岂不是有窄化革命史研究范围的嫌疑?若要成为一个更富创意的学术概念,“新革命史”是否可以增强其包容性,摆脱“新中共革命史”的印象,致力于理解近代中国的各种革命运动?20世纪初,孙中山将自己领导的革命分为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实则尚有思想革命、宗教革命、家庭革命、婚姻革命、史学革命、文学革命、诗界革命、心灵革命等等绚丽多彩的革命。诸如此类的革命现象,似乎都可成为“新革命史”的学术阵地。即使是耳熟能详的20世纪“三大革命”(即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也可再转换思维,发现新天地。比如,一场革命,有革命方,必然有革命的对手方。通常认为,革命方是革命者,而革命的对手方则是被革命者、反革命者。但这很有可能是低估了近代中国革命复杂性而造成的误解,实则20世纪三大革命的对手方也是中国革命运动中的某一段的参与者甚至主导者,也就是说,他们也是革命者。有趣的是,在李金铮与陈红民讨论“新革命史”的时候,已涉及到了这方面的内容。这充分显示,“新革命史”有成为一个开放性学术概念的可能性,因此笔者乐意就一己所见,在这方面多谈一谈。写作的态度,跟陈红民和李金铮两位一样,是为了活跃革命史研究的气氛,推动革命史研究的进步。
一、国民党的历史是“新革命史”的一部分
在2018年举办的“多元视野下的中共苏维埃革命”学术研讨会上,陈红民做了一场大会发言,后经整理扩充,以《“新革命史”学术概念的省思:何为新,为何新,如何新?》为题,发表于当年《苏区研究》第5期。这是“新革命史”概念提出以来第一篇正面商榷的文章,认为既然只有研究方法的进步,而在研究的核心内容方面并无变化,就没有必要在“革命史”前面加一个“新”字;“新革命史”的重要方法创新是引入社会史的方法,但过于强调从其他学科借用方法,有“学术自卑”的嫌疑;并且,李金铮所阐释的“新革命史”的方法并不新鲜,因为这些方法乃是“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普遍趋势,各领域的学者均做过不同程度的努力”;被李金铮称为“新革命史”代表作的一些作品,其作者并无“新革命史”的自觉意识,有点“被‘新革命史’”了的味道。他还为“新革命史”的完善,提出了四点建议。
针对陈红民的质疑和建议,李金铮一一作了回应。笔者最感兴味的,是两位关于国民党的讨论。
陈红民在文章开头说,他的学术专攻是国民党史与蒋介石,“对于革命史的研究我虽关注,但没有任何的研究成果”。他对“新革命史”所提的第四条建议,是“借鉴学界研究革命对象的成果”,为此,他论述道:“民国时期,几乎中共所有的重大事件、政策与决策,深究其背后,大都能找到国民党的因素。国民党是中共革命的主要对象,要全面认识共产党革命的历史,必须了解国民党的历史。如果没有国民党及其政权的存在,共产党的革命历程(包括其艰难性和曲折性)肯定会大不相同。”这些论述给人的印象是,作者认为中共才是革命者,国民党则是革命对象,因此,研究国民党的历史不是研究革命史。
本来,李金铮此前所论证的“新革命史”,就是关于中共革命史的,因此,陈红民的说法,与李金铮的主张是吻合的。以此之故,当看到李金铮在回应文章中的如下论述,笔者难免有点讶异:
要全面认识共产党革命的历史,就必须了解国民党的历史,这是从对立面的镜像中反观自身历史的有效方法。革命与反革命本来就是难以分割的对立统一体,任何一方的研究都可以促进对方的研究。笔者所提出的“加强区域和层级间关系的研究”,正是提醒这一方法的运用。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的历史不仅仅是共产党的对立面,它也曾有过 “革命”的历史,原本就在“新革命史”的范围之内,只是迄今少为注意罢了。
讶异之余,更多的是惊喜。这一段论述表明,虽然李金铮在这篇文章里还在重申此前的观点,宣称自己提出“新革命史”的概念,为的是“对中共革命史进行重新审视,以揭示中共革命的运作形态尤其是艰难、曲折与复杂性”,但其实在他心里,“新革命史”已有更大的关怀,因为国民党的历史既然属“新革命史”的范畴,则“新革命史”显然不仅仅是中共革命史。
不过,国民党的历史属新革命史的范畴,这并非李金铮的回应文章探讨的重点,而像是灵光一闪的产物。那么,该如何看待国民党与革命的关系?国民党谈自己的历史,总是追溯到1894年成立的兴中会,而兴中会及其后的同盟会,无疑是清季革命派的主体,辛亥革命的成功,与这一派的努力密不可分。辛亥革命之后不久,又有“二次革命”,以及护国、护法诸役,都属革命事业。至于改组之后发动的北伐战争,更是以“国民革命”或“大革命”之名载入史册。这一些,无疑都属国民党曾经有过的革命行为。那么,1927年奠都南京之后呢?在“传统革命史”的敘事里,国民党“清共”之后就变成了反革命,不再是革命者。但实际上,1927年之后的国民党也长期以革命者自居。蒋介石的爱将陈诚在其回忆录里提到一件有趣的事: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之后,陈诚于1月21日赶到杭州,向蒋介石请示今后的施政重点,究竟是“行宪”还是“革命”?蒋介石沉吟了一会,很肯定地说:“我们当然要继续革命。”通常认识中的“反革命头子”蒋介石,在一败涂地的时候,居然说出“继续革命”的话,真是一件颇有意味的事情。从这一记载来看,至少蒋介石自认为是革命的。他在“革命”前加了“继续”二字,说明他自认为已经革命了一段时间了。同书还记载,在蒋介石说“当然要继续革命”之前不久,面对中共军队的凌厉攻势,陈诚说过这样的话:“现已至与反革命者短兵相接之时,亦至革命者与不革命者之分水岭。反革命者无时不想阻挠革命,但真有革命之决心者,必将因此而益增深刻之认识与努力。”显然,他所说的“反革命者”是中共,中共所阻挠的“革命”则是国民党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