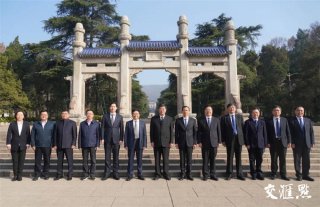宋教仁的东京岁月(3)
辛亥革命网 2022-03-21 13:41 来源:汕头大学学报 作者:徐静波 查看:
同年7月首次启程去中国,在香港和广东游历,9月上旬返回横滨时,在陈少白的寓所邂逅了孙中山,这是两人的第一次会面,从此结为终生同志。
宋教仁抵达东京时,滔天已是中国革命的热心支持者甚至是参与者,与留日学生为主体的革命志士来往密切,并在1904年11月认识了自上海流亡到日本的黄兴。
宋的日记中第一次出现滔天名字的,是在1905年7月17日:
“得程润生来片,言宫崎滔天约于19日上九时与余会见。”程润生(1874-1914),名家柽,1899年秋来日本留学,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农科,革命志士,后来是同盟会骨干,与宋一同参与《二十世纪支那》的编辑,与日本的援华志士多有交往,后来经历坎坷,屡遭蒙冤,辛亥革命成功后,宋教仁专门撰写了长文《程家柽革命大事略》,满怀激情地颂扬他的革命事迹,两人情谊深厚。
滔天也在《亡友录》中撰有《程家柽君》一文:
“他与我的相识,是在明治36年(1903年)的时候,在留学生的知己中,是结交最早的一个。他作为官费留学生,当时在(东京帝大)农科大学读书,支那的革命主义,将我们连结在了一起,我们的关系,胜过兄弟。”于是程家柽在与宋相熟之后,就想到了将其介绍给滔天。
宋的7月19日日记中,对这次会见有详细的记录:
“与润生同赴宫崎滔天之约。……一伟丈夫,美髯椎髻,自外昂然入。视之,则滔天君也。遂起与行礼。润生则为余表来意,讫,复坐。滔天君乃言‘孙逸仙不日将来日本,来时余当为介绍君等’云云。又言:‘君等生于支那,有好机会,有好舞台,君等须好为之,余日本不敢望其肩背,余深恨余之为日本人也。’又言:‘孙逸仙所以迟迟未敢起事者,以声名太大,凡一举足皆为世界所注目,不敢轻于一试。君等将来作事,总以秘密实行为主,毋使虚声外扬也。’言次复呼取酒来,遂围坐而饮之。滔天君又言:‘孙逸仙之为人,志趣清洁,心地光明,现今东西洋殆无其人焉。’又言:‘现今各国,无一不垂涎于支那,即日本亦野心勃勃。日本政党中始终为支那者,惟犬养毅氏一人而已。余前往支那一切革命之事,皆犬养氏资助之。现今大隈重信之政策,皆其所主张者也。孙逸仙亦深得其助动力,盖纯然支那主义者也。君等既有作事之志,不可不一见犬养毅氏,余当为介绍。’至下午四时,始饮酒毕。”
自此,宋教仁与滔天便常有往来,在1905年7月30日举行的中国同盟会创建会议上,宋教仁和滔天都是主要的参加者,8月13日在东京饭田町富士见楼举行的留日学生孙中山欢迎会上,宋是主持人,滔天作为日本嘉宾致词。
在1906年9月5日由宫崎滔天等创刊的《革命评论》上,滔天发表了长文《有关支那留学生》,文章由各个小论题组成,其中批评了不少日本人借中国人来日本留学的热潮从中牟利的劣行:
“尤为令人悲哀的是以营利为目的的支那学生教育也。日本虽然国土狭小,但也是一个以东亚先觉为己任的国家,富豪虽不众,也并非没有驰名世界的人物,我们希望他们能为支那人建造校舍,聘请良师,对其循循善诱真切启发,然事实却是,人们制造了种种借口来趁机榨取学生,以教育作为中饱私囊的工具,这样的人滔滔皆是!”文章对中国留学生充满了期待:
“他们自己已经觉醒。他们已经自己来寻求新学。已经无需对他们加以灌输,只需对他们进行激励,给他们鼓劲,由此来建设一个新支那国。不不,他们自己已经在着手建设了。”滔天还颂扬了吴樾等革命烈士,断言中国已经觉醒,革命就要成功,并正告上之政界要人下之平民偷儿的日本人,不要再鄙视中国人,眼下在日本的年轻的留学生,不久就是新中国的建设者。
宋教仁读到了这一期的《革命评论》,尤其对滔天的长文尤为感服,他在9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
“又接青山屋转寄来《革命评论》报一份,不知何人寄来者,拆视之,则所记皆政治的革命、社会的革命之论文、小说、记事,而尤注重于中国革命运动,其编辑人则题曰宫崎寅藏者也,余始悟此报为宫崎兄弟等所组织,不胜欣慰之至者久之。其中有《就支那留学生》一篇,言中国革命主义之盛及留学生之不可侮,中有论及吴樾、陈天华、史坚如为国捐躯、慷慨就义之处,余心亦感动,不觉泪下良久也。”吴、陈、史三位,都是宋的亲密同志,尤其是陈天华,与宋一样来自湖南,1905年12月8日为抗议日本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不合理规则和《朝日新闻》用“放纵卑劣”的词语来污蔑中国人,在东京湾投海而死。
宋获悉后悲恸不已,在陈的《绝命书》跋中写道:
“每一思君,辄一环诵之,盖未尝不心悁悁然而悲而泪涔涔然下也。”后来又专门撰写《烈士陈星台小传》,颂扬陈“少时即以光复祖国为志,不事家人生产作业,虽箪瓢屡空,处之怡然,日惟著述以鼓吹民族主义;近年革命风潮簸荡一时者,皆烈士提倡之也。”因此,滔天的文章激起了他的强烈共鸣。
宋后来知晓,《革命评论》是滔天专门给他送来的,于是他在日记中写道:
“写致宫崎寅藏信,谢其送报,并请其每月送阅一份,改日即付上报资也。”由此可知,宋教仁与滔天彼此识见的契合和精神的融通,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国界,在打破旧世界、建设新东亚(宋的心目中其时主要还在于建设新中国)的目标上,成为了彼此共鸣和欣赏的同志。
滔天是一个浪迹天涯的侠客般的志士,他对中国革命的倾心支持,一半是出于政治信念,一半也是由于他的侠士般的正义感和热情。
当时宋教仁在同盟会中的地位并不很高,滔天与他的交情也不算很深厚,但当宋教仁由于革命工作的繁忙、在异域的紧张感以及青年期心理的敏感和躁动而在1906年患上了较为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时,他热情地伸出了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