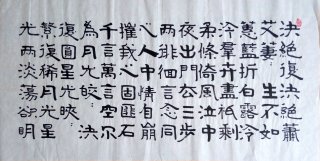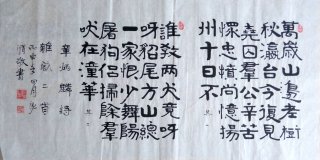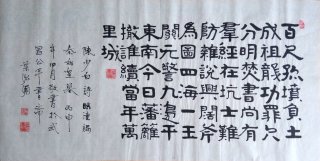我的父亲与党的东北军工作
辛亥革命网 2021-12-12 08:39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朱佳木 查看:
编者按:今年是西安事变85周年,特转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朱佳木在2016年12月12日,在党的东北军后代联谊会纪念西安事变80周年座谈会上,作的《我的父亲与党的东北军工作》的大会发言。该文曾被《百年潮》杂志以《朱理治与党的东北军工作》为题,发表于当年增刊第2期《纪念西安事变及和平解决80周年专辑》上。现在本公众号转发,以纪念西安事变85周年,铭记朱理治老前辈为党的东北军工作及西安事变作出的杰出贡献。
今年是西安事变80周年,《百年潮》杂志社知道我的父亲朱理治当年从事过党的东北军工作,故约我写一篇纪念文章。
我父亲去世较早,生前很少对我们讲他的那段历史,只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受冲击,经常被机关造反派勒令写“历史交待”,还要为其他受审查的干部写历史证明材料,有时需要我帮他做文字工作,所以向我讲述了一些有关东北军工作的情况。他去世后,我又在有关部门编辑纪念他文集的过程中,看到了一些他做东北军工作期间的电报和报告,因而使我对他的那段经历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我父亲从中央红军到陕北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参与党的东北军工作约有一年零五个月。其间大体可分为三段:第一阶段是1935年11月至1936年5月在中共陕甘省委书记任上做东北军工作;第二阶段是1936年5月至8月在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任上做东北军工作;第三阶段是1936年8月底至1937年3月在中共中央驻东北军特派员任上,前往西安帮助东北军做政治工作,同时负责领导东北军的地下党组织。通过对他这三段经历的了解,我得到了一个总的印象,那就是西安事变虽然具有突发性,但也蕴含很大的必然性;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事变前虽然没有告知我们党,但他们能够毅然举事,则是我们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逼蒋抗日”方针的作用,以及我们党对东北军长期深入工作的结果。
要说我父亲参与党对东北军的工作,还要从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说起。中央红军是1935年10月中旬抵达陕甘根据地吴起镇(今吴旗)的,11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将原来的陕甘晋省委改为陕甘和陕北两个省委,并任命我父亲为陕甘省委书记。随后,中央又决定在当地红军游击队的基础上,组建红28、29、30军,任命陕甘省委军事部部长萧劲光和我父亲分别兼任红29军的军长和政委。在1936年2月至5月红军主力东征期间,陕甘省委和红29军的中心任务是保卫和扩大苏区。当时的陕甘苏区从甘肃陇东到陕晋交界的黄河,东西狭长,但南北较窄,只有10个县6万人口;另外,刚成立的红29军大部随红军主力东征,留下的兵力很少,然而进攻苏区的东北军倒有6万之众。面对敌我力量悬殊的局面怎么办?我父亲在他的回忆录《往事回忆》中说,他参加了瓦窑堡会议,亲耳听过毛主席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从中受到很大启发和教育。[ 《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54页。]所以,省委的办法就是按照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集中力量做好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
由张学良统率的东北军是一支“亡国”的军队,虽然被蒋介石先后派往鄂豫皖和陕甘“剿共”,但从上到下充满国恨家仇,弥漫厌战情绪。正因为如此,我们党早在直罗镇战役歼灭东北军一个师又一个团后,便发布了《告围攻陕甘苏区的各部队官长与士兵书》,提出不论哪一派,不论一军一师还是一连一排,不论打没打过红军,都愿与他们互派代表,订立抗日作战协定,组成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联合起来,打日本救中国”;[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2页。]接着,又通过此前红十五军团榆林桥战役俘虏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同张学良本人建立了直接联系,为各级各方面开展对东北军工作奠定了基础。红军主力东征前,张闻天、周恩来多次致电我父亲和陕甘省委,通报东北军情况,指示他们做好东北军工作。[ 《周恩来年谱》(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92页。]为此,我父亲曾派省委白区工作部负责人刘培植代表萧劲光军长,前往省委所在地对面的东北军67军107师,做刘翰东师长的工作。他本人在得知该师参谋长也姓朱后,即亲笔去信,说我们都是朱洪武的后人,不要同室操戈,让外族灭亡中国。省委还指示守卫机关的两个连与107师部队搞联欢,给他们代购给养,相约互放空枪,使这个师“成为东北军中与红军建立友好关系最早的一个师。”[ 刘培植:为纪念朱理治同志诞辰100周年而作,《朱理治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据我父亲回忆,红军主力东征前夕,毛主席曾亲自找他去了解主力走后省委巩固苏区的部署,当听过他的报告后,“表示放心。”[ 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55页。]
红军主力1936年2月东征后,我父亲和萧劲光就做东北军工作的问题,同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彭德怀等中央领导人之间频繁来往电报。仅从公开文献看,那段时间中央领导人直接或间接给我父亲和萧劲光的电报就有10封,而我父亲或以个人名义或和萧劲光联名发出的电报也有14封之多。中央领导人的来电一般是通报上层统战关系达成的协议,询问苏区敌我友三方的动态,指示对东北军在蒋介石威逼下进攻苏区和争取东北军合作抗日方面应采取的策略;我父亲和萧劲光的发电大多是汇报东北军和国民党政训部门的动态,以及做东北军统战工作和巩固、扩大苏区斗争的进展情况,提出对有关问题的请示和建议。例如,1936年3月10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我父亲和萧劲光,告知王以哲要派兵到甘泉换防,我方已同意,指示无论王是否好意,都不得对王部攻击。[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20页。]再如,4月21日,我父亲先以个人名义后以他和萧劲光两人名义,分别给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及周恩来发出两封电报,报告我方与东北军既敌又友、既武又和,以及当地地主豪绅向群众反扑的情况,并提出向西向南扩大陕甘苏区的具体建议。[ 《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6、7页。]时隔3天,张闻天、周恩来复电,表示同意陕甘省委关于和战交错使用的策略,指示他们对国民党政训处的进攻及地方豪绅的反扑必须坚决打击。[ 《张闻天年谱(修订本)》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996页。]我父亲回忆说,红军主力东征期间,他在党内刊物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介绍与东北军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经验,毛主席看到后曾给他写过一封信,给予鼓励。[ 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55页。]
1936年5月初,红军主力完成东征任务,返回陕甘苏区。为配合此后向宁夏、甘肃方向进行的西征,以及进一步做好东北军工作,党中央政治局在5月17日的常委会上决定撤销陕甘省委,成立陕甘宁省委和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陕甘宁省委书记由李富春担任,中央东工委由周恩来任书记,调我父亲任委员兼秘书长,委员中还有叶剑英、李克农、李涛、边章五等人。中央东工委成立不到一个星期,中央政治局又于5月23日召开了一次常委会,专题研究东北军工作。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在听取我父亲的报告后相继发言,总的精神是要在抗日问题上进一步接近东北军,争取东北军中的大多数;强调红军和东北军都是抗日的部队,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对东北军的政策不是瓦解它而是巩固它,要帮助东北军在内部成立抗日会、俱乐部等组织,以团结其左派,打击法西斯反动分子。[ 《张闻天年谱(修订本)》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327页;《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43页;《周恩来年谱》(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17页。]
在中央东工委秘书长的岗位上,我父亲协助周恩来做了两件事。一是参与部署我党在东北军各驻地设立专做东北军工作的委员会或办事处,如在安塞工委下面设立了安塞、枣园两个办事处,在延安工委下面设立了牡丹川、富川、川口三个办事处。其间,他还陪同叶剑英视察过安塞、高桥、下寺湾一线的东线工作委员会(简称东线工委),在安塞、延安召开过两县的东工委会议。[ 《中共东北军党史概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二是参与起草了《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这个文件是中央东工委根据中央政治局5月28日会议关于建立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红军“三位一体”的方针而代中央起草的。文件共6000多字,分十个部分,于6月20日发布。其要旨可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东北军由于所处的亡国奴地位及红军对它的革命影响,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革命的军队;其内部觉悟程度极不一致,正是东北军工作的出发点。第二,对东北军工作的目标不是瓦解、分裂它,也不是把它变成红军,而是帮它在抗日纲领下团结起来,成为红军的友军;对于其在蒋介石与政训处欺骗下的进攻,要给予军事打击,但打击的目的不是消灭它,而是为了争取它。第三,对东北军工作的关键是使其摆脱蒋介石的控制与影响,集中火力进攻蒋介石和政训处;同时,不放弃对政训处的分化工作。第四,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要上层下层同时并进;对上层要接近,竭诚提出我们的主张,诚恳回答他们的问题,协商解决他们遭遇的困难;对下层要从约定互不开枪到互相联络,使他们对进攻苏区的命令消极怠工、敷衍塞责。第五,帮助东北军物色、教育一批自己的积极分子,使他们在内部组成一个坚强的核心组织,并普及到军、师、团中,但不要替它包办一切。第六,要选派最好的同志到东北军内部去工作,秘密发展党的组织,吸收优秀分子入党,但要以抗日积极分子面目出现。第七,凡有东北军驻扎的地方,争取东北军的工作都应是那个地方党的中心工作;要在与东北军有协定的地方设立办事处,并以东北军部队为对象设立流动的工作委员会或特派员,随着部队移动。这个文件对于开展东北军工作起了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此后的东北军工作除了很快根据中央决策将“抗日反蒋”改变为“逼蒋抗日”方针外,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文件的原则而进行的。
文件发出一个月后,中央政治局于7月27日再次召开专题研究东北军工作的会议,由周恩来作了关于中央东工委的工作报告。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这个时期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有很大进步,可谓很好的模范;同时表示,过去工作方针是以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建立联合战线为序排列的,今后要变更一下,“把建立联合战线放在第一位,对东北军、对杨虎城部队、对南京部队,都要建立工作委员会。”[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62页。]周恩来说:“东北军忽视内部的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一般军人对张学良依赖甚深,如张万一被扣,他们便束手无策。建议加强对东北军的宣传工作。”[ 《张闻天年谱(修订本)》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348页。]张闻天说:“工作委员会有很大成绩,说明中央对这一工作指示的正确”;同时提出,要大胆地在东北军中发展党的组织。[ 《张闻天年谱(修订本)》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348页。]
由于此前张学良多次提出希望我党派人去帮助他,加之原属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的东北军地下党(称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组织关系于6月份转给了中央东工委,潘汉年在莫斯科、上海、南京同国民党官方会谈国共合作问题后也抵达了陕北苏区,故中央决定派潘汉年、叶剑英和我父亲三人到西安,同已在张学良身边做秘书的刘鼎一起协助张工作,并将此决定在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化名赵天、赵来、赵古、赵东,于8月9日给张学良的信中通知了他,说“叶剑英帮助军事,朱理治帮助政治工作”。[ 《张闻天年谱(修订本)》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355页。]另据我父亲回忆,周恩来在8月上旬和他谈话说,中央决定叶剑英、彭雪枫和他去西安做东北军工作,叶、彭搞上层统战,他作为中央特派员,领导西安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 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55页。]
此后不久,我父亲即由当时的党中央所在地保安(今志丹县),经东北军占领的延安,到了东线工委所在地安塞。在那里他看到了周恩来留下的几封指示信,也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约定了给中央报告用的暗语,如中央为“钟哥”,东工委为“公司”,周恩来为“董威”,叶剑英为“一兄”等等,他自己化名“玉台”或“王允”。随后,他由从事隐蔽战线工作的刘向三等人护送,于8月30日化装进入西安城,与刘鼎接了头,并由刘翰东师长安排,以东北军学兵队教员名义住进张学良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家里(此时学兵队刚刚组建,编制就放在卫队二营)。在此前后,叶剑英、彭雪峰、潘汉年到西安,也是住在孙家,不过他们都身负多项使命,故来来往往,并不常住,唯有我父亲任务相对单一,一直住在那儿,直到西安事变发生,总共住了103天。
这段时间里,我父亲的工作一方面是不断向中央汇报西安城内特别是东北军的政治动向,以及地下党的情况,分析国统区的形势供中央参考,并请示有关工作的具体问题;另一方面是不断通过东北军地下党组织贯彻中央“逼蒋抗日”的方针(就在我父亲去西安前,中央决定将过去“抗日反蒋”的方针改为“逼蒋抗日”)和有关指示精神,帮助东北军做政治工作,并巩固和发展地下党组织。事实说明,西安的东北军工作完全是由党中央领导的,也都是通过东北军地下党组织进行的,我父亲实际上处于党中央和东北军地下党的一个中间环节。
首先,我父亲在西安的工作,都是根据中央的政策、方针,受中央指示的。而中央的指示一般是经刘鼎的电台(中央与张学良之间早在此前半年就建立了密码联系)和来往于苏区、西安之间的叶剑英、潘汉年等人传达。例如,我父亲到西安第三天,在给周恩来并转中央的报告中就提到:“一兄(指叶剑英)来此,传达中央最近的政治分析与策略运用。我完全同意,并要把这些指示,在我的工作范围内实行起来。”“中央指示‘统一战线越宽越广越好,党的组织越严密越好’,用这种要求作为尺度来考察此地的党,还是相差很远。”[ 《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页。]在1936年11月4日的报告中又说:“周来信指示关于同志会的性质、其与救亡会之关系及党对它的策略,对于我们很重要,我们完全同意。”[ 《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其次,我父亲对于党中央政策、方针和指示的贯彻,都是通过东北军地下党即西安东工委进行的。他到西安后,很快和东工委书记刘澜波接上了关系。那时,东工委领导班子成员中还有孙达生、苗勃然、宋黎。在西安的头一个月,我父亲每周在刘的堂兄东北军105师师长刘多荃家中与刘见一次面,了解情况,布置任务。后来,我父亲和东工委的领导班子在西安郊外还开过几次会,由他根据中央文件讲解时事政策,同时讨论地下党的工作。由于东工委领导成员在东北军中都有公开身份,所以11月绥远抗战爆发前后,刘澜波、苗勃然、孙达生等人被分别调离西安。此时恰值蒋介石飞抵西安,部署西北“剿共”,为贯彻党的“逼蒋抗日”方针,我父亲便和留在西安并在东北民众救亡总会、西北学生救国联合会中有负责职务的宋黎天天到公园接头,布置西安的救亡运动。他回忆说:“从11月下旬到西安事变前的二十天,西安几乎每天都有学生游行示威。”[ 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56页。]
在帮助东北军的政治工作方面,东工委的工作主要是根据中央的政策、方针、指示,推动和参与张学良建立以他为核心的东北军秘密政治组织——抗日同志会,引导东北军学兵队接受抗日和进步的教育,组织地下党员以合法身份到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王曲军官训练团讲课、做宣传,安排地下党员掌握东北军中的东北讲武堂同学会的领导权。
我父亲到西安之前,成立抗日同学会已在酝酿之中。他和叶剑英商量并报经周恩来同意,决定支持张学良建立这个组织,批准刘澜波、宋黎等中共党员加入其中,并可进行入会“宣誓”。[ 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56页。]抗日同志会于1936年9月正式成立,张学良亲任主席,初期只有13人,共产党员占了8人,但其核心始终是东北军的总部参秘室主任应德田和孙铭九等东北军少壮派军人。我父亲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多次提到这个组织的事。9月2日报告说:“现在同志会已经开始,只是这种组织与目前政治上的问题犯了同一种毛病······把它看作比CP(指中共)还要严密。”“我意使这个组织成为我们过去所要求的张学良自己的政治团体。”[ 《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11月4日报告说:“东北军中目前急迫地需要有一个本身的领导的组织,这在今天是不能由党来代替,而必须由东北军本身中的优秀与先进的左倾分子组织起来,才能成功······但他们对于我党的同志都有很大的戒备,而他们本身又不能使自己的工作发展起来。”[ 《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12月3日报告说:“在我校(指中共地下党)的推动下,现在同志会小组是编成功了,五个小组长内,有我们四个同学(指中共党员),并且吸收了我们两个同学参加了中央委员,并通过了两个月扩大120人的计划,这表示出同志会是开始转变了。”[ 《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到12月初,有四个师长加入了同志会。[ 《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
成立学兵队是张学良受宋黎建议创办东北军陆军学校的启发而想出的主意,他认为蒋介石不会同意办陆军学校,但招收学生当学兵、办学兵队还是可以的。他把这件事交给应德田和孙铭九等亲信具体实施,从1936年8月开始筹办。第一期学员是从北平招收的80人,东工委将其中的28个党员组成了一个支部。接着,第二期130人、第三期300人也陆续到来。三期学员中共有150个党员,我父亲和刘澜波商量,让身为东工委宣传部长的宋黎分管党在学兵队中的工作,并在学兵队中成立了一个总支部。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还提到,从北方局选送来的学兵队党员中抽出八位,办了一个训练班,准备分到各军、师中去。据后来宋黎回忆,这八位党员中有徐明、窦子安、赵化南、金明等,由刘澜波和他出面推荐,直接分配到了东北军部队。[ 宋黎:《我所了解的东北军地下党》,载《党史纵横》。]毛泽东对学兵队十分重视,曾在给刘鼎的电报中提出:“学兵队的教材,可请理治编,教员由南(南汉宸)、波(刘澜波)找平津的同情分子担任。”[ 《中共东北军党史概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9页。]我父亲但考虑自己在西安是秘密身份,不便出头露面,加之备课耗费时间、耽误工作,所以只以大学教授名义,到学兵队讲过三个小时的社会发展史。[ 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56页。]
东北讲武堂同学会是当时东北军中最大的群众组织,有两千多名会员。它于1931年成立,后来张学良将东北地区各种军事教育机构都并入其中,亲任总监,故东北讲武堂同学会与张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为了帮助张学良巩固东北军,我父亲与东工委商量,让地下党组织掌握其领导权,推动它健全总会各部门工作,在各师建立联络员制度,进而成立分会,并准备条件成熟时,使其整体加入抗日同志会。另外,还准备成立一个妇女问题研究会,“把东北军的军官太太也组织起来。”[《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页。]
1936年6月,张学良为培养东北军的骨干力量,在西安郊区王曲镇创办了一个军官训练团,每期集训一个月,第一期有120名学员;从第二期开始,第十七路军的军官也加入其中,每期500多人。张学良、杨虎城经常去训话,鼓动学员的抗日情绪。蒋介石也很注意这个训练团,于10月下旬到西安时,还专程去训了一次话。我父亲在11月4日的报告中汇报了这件事,写道:“蒋在军训团讲话中,除前电数点外(未见到这份电报——笔者注),并谓‘谁要对剿匪动摇,谁要提出联俄、联共,我一定要打倒他。’蒋之演说,在军训团中发生了极大的不满。”他还说:“在蒋未来之前,利用我们影响下的报纸做了一些宣传,欢迎蒋来领导抗日。蒋在军训团发表演讲之后,我们影响与领导下的一些报纸作了一些批判,并写了两个演说稿子,到军训团中找人演说,批驳蒋之演说。”[《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鉴于军官训练团的抗日倾向,只办了四期便被蒋介石勒令解散了。
在负责领导东北军地下党方面,党中央交给我父亲的一项主要任务是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他刚到西安时,东工委仅有一二十个党员,在10月11日给中央的报告中,他称赞东工委“组织虽小,但活动范围很大,同志一般都积极干练。因此,党在多种群众组织中以及最近各方面活动中,起了积极的领导作用。同志的情绪很高,个个活动能力都不坏。”[ 《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页。]由东工委领导介绍入党的解方、贾陶、王再天、栗又文等东北军总部的校级军官,也都深受张学良的信任和器重,在各自岗位上积极而巧妙地为党工作。在中央正确方针和有关地方党组织的共同努力下,东工委的组织发展很快,据我父亲1937年3月东北军东调时给中央的报告,那时党员数量已达到二百三四十人。
在党的工作方面,我父亲的另一项任务是通过东工委推动建立和扩大党领导的群众组织,影响和掌握宣传舆论工具。10月上旬,东工委以抗日同志会青年部的名义,发起成立了东北民众救亡会。我父亲在成立大会召开当天的10月11日报告中说:在召开筹备会时,到会17人,包括东北军总部办公厅主任洪钫派,左派群众和地下党组织的代表。这个组织“是比较同志会更带群众性的。我们正和东北军的其他派别谈判,吸收更多的派别下的群众来参加,同时,决定把这个组织完全公开,准备到国民党政府登记去······我们现在决定,仍使这个组织偏重在青年方面,同时在目前同志会极端关门的情况下,把它变成东北民众总的群众性质的组织。这个组织的前途是很大的,我们现在已取得了这个组织的领导权。”[ 《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页。]在这个报告的补充部分,我父亲又汇报了成立大会的情况,指出:“这是抗日运动中很有意义的一件事,表示东北民众由散漫而走到团结一致抗日。它的成立同时给予了西北抗日运动以很大的推动。它已争取到西安公开存在的地位。这表示此地幼年的党,已能够在中央新的策略之下,开始担负起建立东北军内的抗日统一战线的任务。”[ 《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页。]11月4日,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又提到“东救会”,说它已扩大将近300人,“急需打入军队中”,[ 《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一些军、师单位已允许它派人去活动。在12月3日的报告中,他说已有八个团长参加了“东救会”,并把王以哲、董英斌、吴家象等东北军上层人物也“拉了进来”。“东救会”还派出三个代表,见了国民党陕西省主席邵力子,“邵表示他同情共党的联合抗日的主张,他很希望共党有人来和他谈谈。”[ 《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另外,东工委趁张学良改组东北军机关报《西京民报》的机会,推荐了一批中共党员,如魏文伯、陈翰伯等人过来,在宋黎领导下成立了一个党支部。同时,我父亲还遵循党中央的政策、方针,注意纠正错误偏向。例如,他在12月3日的报告中说道:要“尽力纠正宣传及行动中‘左’的倾向,如《西京民报》等公开反蒋的文章,及西北各界救国会筹备会的狭隘工作方式。”[ 《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
为了贯彻中央“逼蒋抗日”的方针,东工委利用一切机会发动群众请愿、示威、游行。我父亲在10月11日报告中汇报了地下党组织利用纪念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策划东北讲武堂同学会动员200多会员向张学良请愿抗日的事。他说:为了防备法西斯(指国民党特务机关)出来压迫群众,有一部分人带了武器。东工委还策动东北大学西京校友会、东北讲武堂同学会等团体发起万人集会,大会发了宣言,会后游行到“西北剿总”,由学生递交了“上副司令(指张学良)请愿书”。张学良身着军装出面接见,激动地表示收复失地的决心。10月,鲁迅逝世,东工委与西安地下党组织通过组织鲁迅追悼会,举行了要求反对内战的群众集会游行。11月,绥远抗战爆发,东工委和中共西北特支领导“东救会”、“西救会”和西安学联等群众团体掀起了援绥高潮。针对蒋介石在西安做出的援绥表示,我父亲在11月4日的报告中说:“目前时局若无其他变化与重大压力加于蒋氏,则出兵援绥,很大可能成为一种姿势与手段,表面上领导抗日,而实质上是拆散西北联合战线,进攻红军与解决东北军。在这种形势之前,我们决定此地党的策略是:帮助东北军的巩固,反对它的破坏者;推动西北统一战线的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来逼迫南京改变现在的态度。”[ 《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2页。]报告中还汇报了几项具体工作,如由“东救会”发起,向蒋介石写请愿书,召集24个团体的代表签名等等。“推动西北联合,组织援绥联军,决定G(指高崇明)同志推动杨(指杨虎城)。”“G以语激杨,杨谓西北局面,张(指张学良)负领导地位,如张干,彼一定受他领导。”[ 《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12月3日报告中,他说依照中共“前次来信所提示”(未见到这一指示信——笔者注),“抓紧了扩大援绥的运动,使军民的注意力集中到绥远问题。”“首先,‘东救会’发起募捐,并派了代表到绥远慰劳。”“在西安我们所领导和影响下的报纸,除《西京日报》之外,都能够抓紧这一运动扩大宣传。”“全西安的绥战后援会(即各界救国会)已经有20多团体发起,日内即可成立。”“蒋二次来,此向下正准备大的请愿运动。”[ 《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页。]
蒋介石再次来西安后,进一步逼迫张、杨“进剿”红军,提出否则要将东北军、西北军调出陕甘,且私下决定让蒋鼎文、卫立煌取代张、杨。张、杨向蒋哭谏无效,遂考虑“兵谏”。12月9日是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东工委和中共西北特支发动“东救会”、“西救会”、西安学联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游行。12月11日,即西安事变爆发前一天,我父亲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详细汇报了这次行动的情况:“请愿示威一共动员了5000多人(实际去了一万人——笔者注),学生居多;还有不少民众。东北军及‘绥署’(指国民党‘绥靖公署’,由杨负责)的士兵表面上是来防备,实际上也部分的参加,并保护这个请愿。向邵力子请愿时,邵的答复,学生表示不满,结果学生驱走了他,以后又冲出了北门,到临潼向蒋请愿。直走到灞桥,与军队相持不下。后张去,完全接受了学生要求,并表示一星期内,一定给各同学事实答复。”报告中还说到下一步的计划:“这星期内,准备:(1)把后援兵(指援绥)正式成立起来。(2)组织绥战义勇队,出发援绥。(3)广泛宣传,组织游艺宣传大会。待下星期张答复后看情况,准备更大的向蒋之请愿活动。”“第二个方法,便是设法动员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将官、士兵,请缨、请愿、签名,以至于士兵的(骚)动。”[ 《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然而,这些计划还未等实行,张、杨就在第二天扣留了蒋介石,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项主张,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张学良即电告中共中央。党中央立即复电,除答复军事部署外,表示周恩来拟去西安“协商大计。”12月16日,在东工委和中共西北特支共同策划和领导下,西安举行了十万人集会,支持张、杨的义举,张、杨上台讲话,申明主张。17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20日,周在孙铭九家中听取了我父亲的汇报,指示他继续担任中央特派员,领导东工委,同时参加陕西省委,并搬出孙家,在外面另立机关。[ 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56页。]这时,西安事变虽然得到了和平解决,但因张学良陪蒋回南京被扣,引起东北军内部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分裂,发生了应德田、孙铭九等主战派军人枪杀王以哲将军的“二二”事件。为防不测,中共代表团除周恩来外,均于2月3日撤出了西安。二二事件前,我父亲患肺炎住进了医院,故代表团中负责与他联系的博古撤离前,专程到医院看望我父亲,告之已安排东工委在他高烧退后即护送他出城。2月10日左右,东工委弄来一辆卡车,由东北军团长、地下党员贾陶带着几辆摩托车,护送我父亲出了城,辗转到红军总部所在地三原县云阳镇养病。
3月底,我父亲在耀县召集东工委刘澜波、宋黎、高锦明等人开会,研究东北军东调后的工作及人事安排,然后到西安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得到批准后,正式形成了向中央书记处的书面报告:“东北军工作近况及新的布置”,以及附件“‘双十二’事变中东北军党的活动的教训”。[ 《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31-38页。]4月底,我父亲回延安参加党的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代表会议,并在会议期间写出《东北军工作经验总结》,由中央秘书处印成小册子。[ 《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57页。]5月初,中央任命他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当时的河南省委兼管皖北、苏鲁边、豫鄂边党的组织,而这些地方刚好是东北军东调的新驻地,故他赴任后,也参与了对原东北军部队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工作,不过这方面情况从已公开的资料中仅看到零星披露。
前面已经说过,从我父亲做东北军工作的经历清楚地看出,西安事变虽然是张学良、杨虎城两人商量决定的,但却是在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和“逼蒋抗日”方针的作用下,在党的东北军工作的推动下发生的。它充分说明了,我们党的确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我们党和中华民族一切深明大义的仁人志士,为着中国的自由、独立和富强,不屈不挠地奋斗,都付出了巨大牺牲。我们今天纪念西安事变80周年,最重要的就是铭记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推动张学良、杨虎城转变立场、团结御侮所建立的丰功伟绩,铭记张学良、杨虎城、王以哲等爱国志士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所作出的历史贡献,继承和弘扬他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继续奋斗。
(本文刊载于《百年潮》2016年增刊第2期纪念西安事变及和平解决80周年专辑。作者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