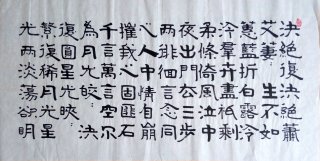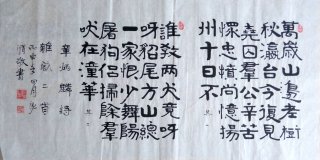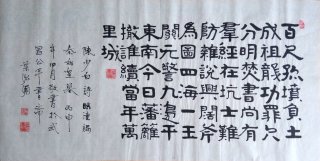冯天瑜:尽瘁辛亥首义史的贺觉非先生
辛亥革命网 2021-10-10 10:46 来源:《月华集》 作者:冯天瑜 查看:

湖北是声色壮丽的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舞台。这里曾经是林则徐义无反顾地推行禁烟运动的起始处,太平军与湘军反复较量的“四战之地”,洋务派后期巨擘张之洞实施“新政”的基点,自立军起义并遭屠戮的所在。当人们历数湖北近代发生的重大事件时,都不会忘记,20世纪初叶,反清革命运动曾在这个省份风起云涌,省垣武昌爆发结束中国两千余年专制帝制的新军起义,将以孙中山为旗帜的奋斗多年的革命运动推向高峰。武昌首义作为辛亥革命的一个关键环节彪炳青史,它从酝酿、爆发、扩展到失败的历程,相当充分地显示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若干基本特征,因而成为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典型案例,为众多中外史家所关注。同时,这段史事浓郁的地方人文色彩,对热爱乡邦者尤具魅力。三烈士纪念碑、彭刘杨路、首义路、首义公园、起义门、阅马场湖北军政府旧址、拜将纪念碑、蛇山头黄兴铜像是我这样的“老武昌”从幼年时代起便经常流连徜徉的处所,时至壮年,每当重游首义胜迹,仍然会激起异样的热情。至于首义先烈的故事,连同其中包蕴着的爱国主义和民主精神,则通过前辈的讲述和书本上的文字,如同“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滋养着吾侪心田。与辛亥武昌首义密切相关的张之洞、吴禄贞等人物的思想行迹,也对我有着特别的吸引力。
正是上述一切,培植了我对辛亥武昌首义及前后史事的拳拳情怀,并驱使自己从致力史学工作之始,便有意探究这段悲壮而又曲折多致的历史,20世纪70年代末期还产生过用小说形式表现辛亥武昌首义的设想,并曾形诸文字,终因自忖短于形象思维而没有继续下去。
正当我在寻觅钻研辛亥武昌首义史的升堂人室之径时,经由先父的朋友张云冕先生介绍,于1980年初结识长期从事辛亥革命史料捜集整理工作的贺觉非先生。
岁月的流逝,已经模糊了初识贺先生具体场合的记忆,但贺先生的风趣谦和、谈锋甚健使我们的首次会面立即变得亲切融洽,这一印象则鲜明如昨。他同我交谈几句后,便操着竹溪乡音大声说:“我知道你,你是华师一附中的高才生。”此时我才得知,时年七十的贺先生曾经是华中师院一附中的历史教员,19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当阳县草埠农场劳动;而我恰恰在该年进人华师一附中念高中,长期以来没有听说过贺先生其人其事。若非撰写《辛亥武昌首义史》的因缘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相逢,则几乎同这位老师失之交臂。
贺先生接着说,他已从张云冕先生处得见我撰写的有关武昌首义的论文,以为所见略同,并笑着说:“吾道不孤。”贺先生还兴味盎然地讲述他自50年代中期以来受湖北省政协委托,广为接触首义老人,搜集整理辛亥武昌首义史资料,主持编辑《辛亥首义回忆录》1~4辑的情形,特别绘声绘色地谈及他与李西屏、李春萱、熊秉坤、张裕昆、杨玉如、耿伯钊、李白贞等武昌首义参加者交往的细节。我则回忆起,耿伯钊是我们家的老邻居。我小时候见过耿伯钊身披黑色斗篷,手执拐杖的挺拔军人气度。贺先生说,耿1957年也被打成右派,晚境悲凉。贺先生感慨道:"现在首义老人只有赵师梅、喻育之硕果仅存了,而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首义老人健在者居于武汉市的,不下600人,我与他们几乎都有程度不等的交往。”以后我得知,贺先生还同首义老人的子女辈建立深厚友谊,辛亥后裔们常到贺老这里询问老辈往事’贺老则诱导他们回忆老辈行迹,鼓励他们捐献辛亥革命文物,提供有关文献。70年代末、80年代初,贺老成为辛亥后裔聚会、交流信息的枢纽。而且,长期以来,贺先生还是向省里反映首义老人及其亲属苦衷和要求的桥梁,并为他们解决过不少实际困难。今日,许多辛亥后裔成为省、市、区各级政协委员,或民主党派各级负责人,他们的意见比较容易“上传”了,而在80年代初期以前,自身处境并不好的贺先生为辛亥老人及其后裔所做的种种工作,尤其值得缅怀。
大约经过两次商谈,贺先生与我便达成合作撰写“辛亥武昌首义史”的共识。此前,贺先生已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联系,并将自己撰写的“首义史稿”文稿交给该所,拟与之合作撰成“首义史”。但时间过去一年有余,尚未从近代史所获得明确回应。自感来日无多的贺先生决定另觅合作者,并拜托我去北京,从近代史所取回他的文稿。约在1980年年末,我专程赴京,造访著名的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这是我第一次前往近代史研究所,由此结识丁守和、王庆成、耿云志、张海鹏、杨天石、王岐山诸君。
近代史所有关同志对长期搜集整理辛亥革命史资料的贺先生都怀有敬意,但他们又明确表示,贺先生的文稿,是一种随感式写法,不具备一部史学专著的修改基础,需要整个重写。而近代史所诸人正忙于“中华民国史”的写作,难以抽出力量改写“首义史”。近代史所诸同志很支持我与贺老合作,但他们善意地指出:“改写这部文稿,其难度可能比自己单独写一本书更大。”近代史所还派时任近代史所助理研究员的王岐山带领我到北京各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查找辛亥革命史资料。记得岐山有一辆当时比较难得的自备摩托车,他驾驶摩托车,我坐后座,奔驰于近代史所、北京图书馆等处之间,历经数日。1995年秋,时任建设银行行长的王岐山来武汉大学主持建设银行“行长班”开学典礼,与我约见,忆及10余年前的这段往事,追怀辞世的贺先生,颇多感慨。
1980年底返回武汉以后,我婉转地向贺先生报告近代史所对他的文稿的意见。正当我于吞吞吐吐不便措辞之间,已经明白意思的贺先生十分坦然,没有流露些许不快,他笑着说:“是的,是的,他们的意见不错。我的稿子,只是一些‘砖头瓦片’。如何建造房子,得靠你的学问才力。你不必有顾虑,只管重起炉灶,另写就是。”贺先生的此等襟怀,赢得了我对他较深一层的尊敬。我们的合作,也就十分愉快地开始了。
贺先生一方面放手让我独自撰写书稿,一方面又多次详谈他所熟知的首义掌故,并悉数拿出他多年搜集的辛亥革命史资料。我由此得知如下情节——
第一,70年代末期,我在广为阅览辛亥革命史论著时,曾读过《光明曰报》史学栏60年代初期刊载的署名“扬苏”“扬樵”的文章《试论自立军事件》和《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文献论略》,留下颇深印象,尤其钦佩后文占有材料的广博,但不知扬氏为何许人,曾向同道探听,也未获所以。而现在贺先生交给我的材料中,便有此二文,于是我即兴询问二文作者何人,贺老呵呵大笑曰:“扬苏、扬樵,即老夫贺觉非笔名也!”他进而解释说,60年代初,他正戴着“右派”帽子,即使摘了帽子也是“摘帽右派”,哪里够格到《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于是以夫人名义投寄文章,署名“扬苏”“扬樵”。谈及此事时,贺先生夫人杨正苏老师也在场,笑得合不拢嘴。杨老师是四川人,为清代嘉道间名将杨遇春(1761-1837,四川重庆人)后裔。杨老师数次向我谈及英武的先祖时,眉宇间都流露出骄傲的神色。
第二,贺先生交给我的他手撰的种种笔记,大都纸质粗劣,有的竟是60年代的香烟盒,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甚难辨识。杨老师特为解释道:“我解放前当小学教员,解放初离职,照料老贺生活。当时老贺一月90多元,两人满好过。1957年老贺被打成右派,工资减半,我又没有收人,生活很困难。1960年前后,买一本笔记本、一沓稿纸都得从牙缝里挤,没得法,老贺就到处拾废纸,捡香烟盒,充作资料卡片用。”这便是贺先生给我的一大沓灰黄色、浅黑色纸片的由来,上面记载着50年代末60年代初贺先生跋涉(这里用的是“跋涉”一词的本义,即徒步行走,因为贺先生那时没有钱搭公共汽车,多为步行)于武汉三镇间,到熊秉坤、杨玉如等首义参加者家中采访的内容。杨老师还告诉我:“反右时挨批斗,‘文革’中游街、抄家,老贺别的都不担心,就怕这些资料损失了,要我想天方、设地法保存好。我也真是这样做的,家里别的什物我都不管,唯独这些破本子、小纸片,我是一本本、一张张收藏得严严实实。现在可好了,这些本子、纸片可以交给冯老师写进书里去了,我的心愿也算了却了。”杨老师每次讲起这一话题,总是眼圈发红。贺先生在一旁却笑嘻嘻地说:“你看你,又多愁善感了吧!现在应该高兴,你保存的材料得见天日了!”
面对着这等来历的资料,面对着如此善良、坚毅的两位老人,我的心震颤起来,暗自决断_困难再大,也要把这本书写好!
我的学术工作辟有两线,一为文化史,一为湖北地方史志,而且前者为主,后者为辅,故不能以较多的时间精力投人“首义史”写作,1981?982年,时断时续,往往是贺先生催促得急,进度稍快,否则进度甚慢。当此之际,贺老于1982年11月18日因心肌梗死辞世。第二天,省政协文史办公室通知我,我立即赶至贺家,泪流满面的杨老师握住我的双手说:“老贺的最大心愿,就是首义史出版。以后就辛苦你冯老师了!”我默默地承接了这位没有后嗣的老人的企望,此后果真加快了撰写的速度,终于在1984年9月完成40余万言的《辛亥武昌首义史》,1985年9月,以贺觉非第一署名、我为第二署名的该书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年该书获武汉优秀社会科学著作一等奖。我先后给杨老师送稿费、样书和奖金时,因无子女而晚景尤显凄清的杨老师总是喃喃地说:“老贺,老贺,您地下有灵,也该安心了!”
应当说明的是,1984年成稿、1985年出版的《辛亥武昌首义史》的文本,1982年逝世的贺老未及亲览。虽然在写作中我曾就一些问题与贺老磋商,但不一定都取得一致意见,而我便先依己见写出再说,本拟留待全稿完成后再同贺老逐一讨论,而因贺老骤逝终于失去这种机会。现在读者看到的《辛亥武昌首义史》的若干论断,如湖北革命团体的肇始应为花园山聚会,而并非之后的科学补习所;汉口宝善里机关失事时间为1911年10月9日,并非10月8日;打响首义第一枪的是程正瀛,而并非熊秉坤;1911年10月10日率先起事的是城外辎重队,而并非城内工程营;早在1911年4月至6月,党人已有举黎元洪为都督之议,首义后黎任都督并非纯属偶然,等等,均与贺老意见相左。这些结论是我广为占有各方材料,加以比较分析之后获得的,虽与贺老一向观点有别,也只能依“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宗旨处置了。相信贺老在冥冥之中,会理解这种做法。
在与贺先生交往的两年间还逐渐得悉他的生平。现以《湖北省志•人物志稿》的《贺觉非传》为线索,结合自己的见闻略记其事迹。
贺觉非(1910—1982),字策修,湖北竹溪县丰溪人。幼年喜读史部,后人武昌中华大学,未毕业即任武昌三楚中学历史教员,不久入中央军校10期学习。1934年,随军委会参谋团入川,任参谋团政训处科员。后调刘文辉部,1940年随军入西康,沿途留心考察形胜人文,成七言绝句百数十首,对山川隘要、民生疾苦多有记述。后又博征文献,撰《西康纪事诗本事注》一卷,重庆史学书局出版。次年任理化县县长。实地勘查山水物产,探访藏胞、高僧、老吏,搜集民俗轶闻,又遍读四川地方志,于1944年修成《理化县志》。足见贺先生探访、记载地方史事的努力,始于青年时代,这是对中国史学一种优良传统的承袭。贺先生1949年后成为辛亥武昌首义史料捜集整理最有实绩者,确非偶然。
抗日战争胜利后贺先生回湖北,任汉口市政府秘书、三民区区长。1947年任竹溪县县长。1949年任新编118军少将高参,随军到成都,参与筹划该军起义。118军起义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贺龙、王新亭、胡耀邦曾宴请118军军长邓锡侯等高级军官,贺先生在座。80年代初,贺先生与我闲谈时说,当年在宴会席间,贺龙在得知贺觉非的姓名后,专门走到他身边,拍着贺先生肩膀说:“老弟,姓贺的不多,你要好好干!”贺先生还几次对我说,1949年成都宴会上的国共两方面人物,如邓锡侯、贺龙、王新亭等,均已作古,现今在世的只剩胡耀邦同志和贺某人了。贺老为此不胜唏嘘。他十分感佩耀邦同志主持中组部时平反冤狱(包括改正右派)的雄才大略,几次对我说,“首义史”印行以后,一定要赠送耀邦。但贺老终于在“首义史”成书之前仙逝;1985年《首义史》出版后,我也曾经想到赠书耀邦同志,以了却贺老遗愿,但因朝野远隔,不便打扰而搁置下来。耀邦同志又于1989年辞世,贺老的赠书意愿终成永远的遗憾。
1950年初,贺先生参加中南军政大学学习。1953年结业后回武汉,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研究员,这是对起义人员的惯例安排,而贺先生认为自己正当盛年,还可做些实事,于是主动争取到中南工农速成中学、华中师院附中任历史教员。1956年,贺先生被邀为省政协第二届委员,受命捜集整理辛亥武昌首义资料,由此开始他孜孜不倦的辛亥首义史研习工作,遂有前述种种事迹及80年代初与我的一段忘年之交。
1977年以后,贺先生相继担任湖北省政协第四届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湖北省委委员、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省地方志编委会编委、中国地方志协会常务理事、武汉地方志编委会编委、省志人物志顾问。值得一提的是,贺先生以丰富的修志经验和渊博的湖北地方史知识,对湖北省、武汉市地方志的修纂工作多有贡献,这是省市方志界的一致评价。贺先生编撰多年,原拟作为"首义史”附录的《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上下两卷,经王岐山整理,1983年3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同年,省地方志办公室刊印其所撰《辛亥湖北人物传》。惜乎这些著作连同《辛亥武昌首义史》,都是在贺先生作古之后方陆续面世的。但这位诚挚勤勉、放达乐观的老人以心血投入的武昌首义资料捜集整理及研究工作,以其切实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必将随辛亥首义这一光辉的史事一同为后人所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