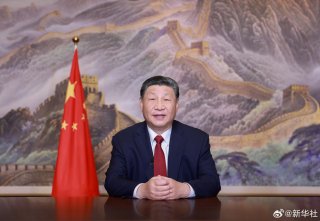法国官方档案中的黄兴(2)
辛亥革命网 2017-02-17 13:54 来源: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 作者:邵雍 查看:
“他们给这些来听说教的人都发给了在本年内已出版了五个月的、在东京印刷的《民报》。
“我与黄兴的会晤非常真诚和有意思。据他看,住在广西的督抚林绍年在等待事件以表态。
“财务部右侍郎唐绍仪是孙逸仙党的加入者;
“袁世凯和广州的总督(指两广总督岑春煊----引者注)在运动一旦发起时,都将被卷入;但我大胆怀疑两广总督会卷入,因为此人经常血腥地处死他所逮住的革命党人;
“龙州道台是绝对地被争取到这个党中来了(他对此向我作了保证,我认为他没有骗我,但我不大知道革命发起时他将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行事)。
“黄兴对我肯定地说,外国人的财产和人身安全都将受到尊重,由于孙逸仙的纲领中甚互有信仰自由这一条,革命党人将不会触及教堂、新教或天主教的传教团,也不会去触及那些属他们管辖的土著天主教徒。惟一的敌人是满洲人,他们以五千万的人数来压迫四亿汉族人(老一套说法)。
“黄兴还向我重复道,孙逸仙是惟一的首脑,只有他一人知道全部计划,由他一人确定发起运动的时间,而且他属于共济会,并在那里找到了支持。孙逸仙和黄兴的第一次见面是在日本,正值秘密会社(哥老会、三合会、大刀会、小刀会等等)以同盟会的名称联合之时。这个党的钱存放在香港的上海银行(即汇丰银行——引者注)。”
这段来自越南河内的法国情报信息量大,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在这封信中有关黄兴的简历与史实大相庭径。黄兴1874年生于湖南善化(即长沙),到1906年是32岁了。虽然黄兴不是他最初的原名,但也决非“假名”。他在青少年时代的主要经历就是读书求学,没有担任过地方“小官吏”,也没有当过根本不存在的“国民卫队的指挥官”。至于在长沙“发动过两次失败的起义”云云也是不正确的。1900年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时,黄兴只是作为朋友有所预闻而已。黄兴真正在长沙策动起义是在1904年华兴会成立之后,而不是在1903年。不过,布加卑在河内代理人对黄兴的第一印象倒是十分逼真传神,与我们看到的黄兴当年照片中的形象是完全吻合的。
信中披露了黄兴的龙州之行特别引人关注。在龙州的短短三天时间里黄兴住在龙州军事学校,确切地说是钮永建任监督的将弁学堂。三天中有两晚与边防督办庄蕴宽道台进行了长时间的会晤,均持续到次日凌晨三点。此外黄兴还秘密会见了指挥边境所有的部队陆荣廷(小名陆阿宋),结果是陆荣廷与他的副职陈炳焜都决定“只要有可能就参加运动。”
在完成了龙州之行后,黄兴返回河内。而某些来不得及去龙州的人都来到了河内与黄兴联系。其中有指挥南关哨所的王姓小军官,有来太平府的两名小军官,还有代表指挥三个营的郑永廷的军官何元诚。此外陆荣廷特派一位姓吴的人作为代表前来河内。
在信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即使在祖国西南边陲黄兴同样有巨大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在广西省,凡是同盟会革命同志对黄兴都十分尊重,全力拥护,向他致敬,并且表示“得到通知的运动时间一到就竭尽全力协作”。
黄兴回河内后,与法军中国情报处处长布加卑的代理人见过三次面。在“非常真诚和有意思”的会晤中,黄兴介绍了一些清朝大员的政治动向,宣称财务部右侍郎唐绍仪已经加入了同盟会;袁世凯和两广总督岑春煊在运动一旦发起时都将被卷入;广西巡抚林绍年在等待事件以表态;龙州道台是绝对地被争取到同盟会中来了。黄兴对此向布加卑的代理人作了保证,但对方还是怀疑龙州道台在 “革命发起时他将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行事”。
(三)
现在有必要对这些新史料来一番解读,拨开历史的迷雾。
首先,黄兴关于与庄蕴宽的会谈,庄本人是不承认的。庄蕴宽云:“光绪三十二年(即1906年——引者注),予督办广西边防。有僧张守正求见,予知为克强(黄兴的字——引者注),嘱岳生宏群接待之,未与面也。钮惕生方为教导团团长,夙与之善,告予,以克强将出国而乏川资,因厚赆之,并派兵护送出镇南关。克强固请一见,予不之许。”这段话是庄蕴宽写于1915年以后,当时已经是民国。在这种历史情境下,清末与黄兴秘密会晤是光荣的历史,完全没有必要再加隐瞒或否认。照庄蕴宽的说法,就是这样没有见面,还受到了袁世凯派人前来追查。辛亥武昌起义后,他作为江浙代表前往武汉,这才与黄兴见了面。因此这段历史细节只能暂时存疑,尚待进一步考证。
其次,黄兴关于与广西边防军“荣字营”统领陆荣廷的会谈。以前只知道同盟会在发动镇南关起义前曾经派人秘密策反陆荣廷。1907年11月镇南关都督王和顺致书陆荣廷,劝其反正。陆派帮统陈炳焜秘密赴河内,向胡汉民表示“统领陆公,素有大志,……中国有事,边防之军,必不为天下后”。其实就组织关系而论陆荣廷是在东京上了同盟会名册的。1911年11月广西独立后,陆荣廷先后任广西副都督、都督。从这点推论,1906年陆荣廷与黄兴直接接触,表态“只要有可能就参加运动”,并密派吴某再到河内与黄兴联系是很有可能的。只是孤证不立,此事也需要其他资料的佐证。
第三,从宏观上说,黄兴不计个人名位,真心实意地维护孙中山的革命领袖地位,可敬可佩。他反复对法国情报人员强调:“孙逸仙是惟一的首脑,只有他一人知道全部计划,由他一人确定发起运动的时间”。法国情报人员也认为黄兴是孙中山“这个首脑的左右手”。黄兴还坚决执行孙中山制定的革命方略,肯定地对法国情报人员保证:“外国人的财产和人身安全都将受到尊重,由于孙逸仙的纲领中甚互有信仰自由这一条,革命党人将不会触及教堂、新教或天主教的传教团,也不会去触及那些属他们管辖的土著天主教徒。惟一的敌人是满洲人,他们以五千万的人数来压迫四亿汉族人”。上述表述,无论思想、语言都是孙中山的翻版与复制,宣传口径完全一致,以至于对方认为此类表述是“老一套说法”。
最后,黄兴1906年5月11日回河内后向法国情报人员通报的清朝高官的政治动向也有夸张之嫌:唐绍仪时任外务部而不是财务部的右侍郎,他加入同盟会的时间是1912年春,而不是1906年夏;袁世凯在武昌起义后是积极行动起来了,但并非卷入革命运动,而是旨在乱中夺取国家的最高权力;岑春煊在担任两广总督期间残酷镇压了广西会党大造反,连布加卑的代理人都对他“大胆怀疑”,“因为此人经常血腥地处死他所逮住的革命党人”。广西巡抚林绍年“在等待事件以表态”之说,具有极大的伸缩性、可变性,无论怎么理解均无问题。至于“龙州道台”一职,严格说是没有的,只不过因为当时督办广西边防的庄蕴宽(兼太平顺思考兵备道)驻节龙州,于是法国情报人员就称庄蕴宽为“庄道台”、“龙州道台”了。庄蕴宽虽然思想开明,一贯同情革命,但似乎也没有到“绝对地被争取到”同盟会中来的地步,至少庄蕴宽本人直至1915年以后都没有认可。辛亥年他充任的“江浙两省代表”从上海前往武汉参加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也不是同盟会的真意。我们认为黄兴在与法国情报人员的交谈中之所以言过其实,很可能是为了虚张革命党的声势,为争取可能的外援烘托气氛,创造一些条件。
总之,法国官方档案中的黄兴形象既有清晰真切的一面也有扑朔迷离的一面,有些难题确实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究,设法破解。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1905-1906年的法国中国情报处的史料价值,相反这些情报提供了新的历史信息与线索,有些还是相当可靠的。如黄兴在两湖地区及广西等地均享有崇高威望与巨大的号召力与影响力;他一身两任,既被看作是哥老会的首领,又被称为孙中山的左右手;他力谋团结,全力辅佐孙中山,宣传孙中山,维护孙中山等等。认真解读这些宝贵史料,可以大大推进黄兴研究乃至整个辛亥革命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