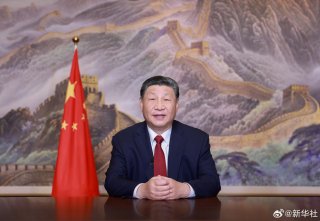炸弹与药方
辛亥革命网 2019-06-28 09:52 来源:中国经营网 作者:雪饵 查看:
南粤的冬天并不寒冷,但在这里却依然充满了阴森。
时已夜半,大厅的四周却依然裹着黑布,不让烛光有一丝的外泄。厅的正中,摆放着一张案桌,包着白布。一支白色蜡烛照亮着桌上一个狰狞的骷髅头。
这并非黑帮的堂口,而是革命恐怖组织“支那暗杀团”的宣誓会场。入盟者必须面向骷髅站立一段时间,然后被告知组织的宗旨和方略。
这是1909年的冬天,香港,一片没有黄龙旗飘扬的大清国土。当然,革命者从不讳言自己对暴力的信仰及对鲜血的无畏,而吊诡的是,似乎总是摆出非暴力柔弱姿态的保皇党,也同样信奉匕首与炸弹。
不择手段
几天前(1909年12月9日),一位名叫刘思复的“恐怖主义”嫌疑犯,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监狱被假释出狱,他迅速来到香港,组建了这个“支那暗杀团”。除了刘思复外,这个暗杀团还有位日后大名鼎鼎的人物:陈炯明。这个组织,迅速得到了革命党的重视,成为革命党手中的一把精钢匕首,摄政王载沣、广东水师提督李准(首位宣示南海主权的中国将领)、广州将军凤山都成为他们的目标,只是刺杀载沣未遂,而李准则被炸成重伤,凤山被炸身亡。尽管日后掌权的国民党,似乎羞于谈论这段黑帮前传,但毫无疑问,“支那暗杀团”成功地建立起了“革命恐怖”氛围。
就在刘思复面对着骷髅头宣誓时,身在日本的另一群年轻人汪精卫、陈璧君等,也组建了一个暗杀团体,他们在日本的主要学业就是制作炸弹,要“藉炸弹之力,以为激动之方”,用恐怖主义挽救革命的颓势。
早在兴中会草创时代,暗杀就成为革命的重要内容。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结合成同盟会后,暗杀组织更是遍地开花,除了刘思复的“支那暗杀团”、汪精卫的“京津暗杀团”外,还有诸如“北京暗杀团”、“天津暗杀团”、“东方暗杀团”、“中国敢死队”等,艰巨而漫长的社会革命被简化成匕首与炸弹的快餐式操作。暗杀这种短平快运作,似乎很容易令人上瘾,从肉体上剪除异己的习性,牢牢地渗透到了革命党的血液之中。辛亥革命之后,暗杀就成了革命党内部路线斗争的有力武器。一位名叫蒋中正的年轻人,通过刺杀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而赢得了革命党的绝对信任,为自己迅速成长为革命、乃至民族的下一任领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革命者从不讳言自己对暴力的信仰及对鲜血的无畏,而吊诡的是,似乎总是摆出非暴力柔弱姿态的保皇党,也同样信奉匕首与炸弹。在康有为的领导下,保皇党耗费巨资进行大量的暗杀行动,虽然没有能消灭“顽固派”,却在党内清除异己方面功效卓著。
即使身在国内,没有条件也没有胆量进行暴力恐怖攻击的立宪派们,为了达成自己的政治目标,也实行一种“非暴力的恐怖行为”:公开号称“不纳税主义”,国会一日不开,各省咨议局就一日不得承认政府的新租税。本应根基于妥协与宽容的立宪运动,成为一种非黑即白的零和游戏,权力资源成为绑架和勒索对手的武器,社会安定与和谐则成为“刀口”下的人质。
“不择手段”越来越成为晚清政治舞台上各种角色的“同一首歌”,各种政治力量都认为自己真理在手、正义在握,都抱持着舍我其谁、唯我独尊的救世主心态,都将别人的执政妖魔化,而将自己的掌权神化为人间天堂。
尽管民国的官修历史,都将一切乱象简便地归咎于清王朝在政治改革上的拖延,但那些吃俸禄的民国太史公们似乎忽视了:在被他们称为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彻底覆没后,急不可耐、并且不择手段地高喊“民主、宪政”的造反者们,“破旧”之后却无法“立新”,依然捡拾起清王朝的“借口”,乃至高喊“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的响亮口号,其“立宪预备”之漫长、中央控制之细腻、领袖集权之严密,令清王朝的遗老遗少们自叹不如。革命派认为“中华”才是病人,而满清当权者本身是病毒,应当清除,才能保中国;而保皇派则认为,爱中国就要爱大清,救中国就是救大清,即使大清国成了植物人,也可以从西方进行政治体制层面上的全面器官移植。
神医遍地
其实,当中国在晚清时病入膏肓,不同的医生开出的是不同的治疗方案:有的认为必须大动手术,才能起死回生,而且时不我待,应立即动刀。革命派和海外的保皇派都属于这一类,区别在于革命派认为“中华”才是病人,而满清当权者本身是病毒,应当清除,才能保中国;而保皇派则认为,爱中国就要爱大清,救中国就是救大清,即使大清国成了植物人,也可以从西方进行政治体制层面上的全面器官移植。另一类医生,则认为正因为病情过重,才不应操切从事,而应采用保守疗法,固本培元,这些意见自然显不出医术高明,没人爱听,1909年下课的陕甘总督升允就是其中之一。有学者将这种面对绝症的截然相反的意见,称为大清改革所遭遇到的“重症综合症”。
如此精到的观点,却毕竟还是从“纯医学”角度出发。被学者们有意无意忽视了的,是大清国这位身染沉疴的病人,却拥有着无限的政经财富。面对一个富得流油而且垂危的病人,你还能指望他得到纯粹医学意义上的关注与治疗吗?于是,良医遍地,药方满天,其间或许真有扁鹊、华佗,但更多的是滥竽充数者和浑水摸鱼者,甚至兽医、屠夫改行,拿着屠刀当做手术刀的。
肥沃的权力牧场一旦抛荒,就会成为城狐社鼠的乐园。打倒了一头被“既得利益”撑饱了肚子的“饱狼”,迎来的或许是10头嗷嗷待哺的“饿狼”。动听的口号如同风月场中的海誓山盟,比短暂的高潮消散得更快、更彻底。利益决定立场、立场决定态度,从来都是屁股指挥脑袋。激进与保守、革命与保皇、左与右,一切归根到底就只是“未得利益”与“既得利益”的分野。在野时高调入云、绕梁三日,甚至恨不能上嘴唇挨着天,下嘴唇接着地;而一旦在朝,则莫不将全天下当做一己的卧榻,“率土之滨,莫非皇臣”,化国为家,以家代国。 “腐朽”的大清帝国灭亡后,“伟大”的民国却丝毫未见病情有所好转,大清国的“流感病毒”似乎并没有随着病人的死亡而消失,反而出现了更为强壮的变种,一而再、再而三地造就着新的案例。
其实,流感早已蔓延全民,尤其是那些到处开方子的真假“神医”,他们本身的能力、素养、动机,他们日思夜想、朝夕相伴着权力这一“病原体”,都注定了他们才是最容易被感染的高危人群。而问题在于,神医们在给别人打针、下药、截肢甚至安乐死的同时,从来就没想过自己也该修理修理。于是,一部中国近代史,俨然就是这种病毒的传染史,“神医”不断成为“病人”,一茬又一茬,前“腐”后继,而中国在不断吃药的同时,也不断期待着宿命中下一个“神医”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