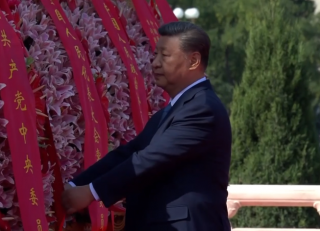谭延闿被迫下台和李仲麟等被杀的回忆(3)
辛亥革命网 2018-07-24 10:30 来源: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集 作者:黄一欧 查看:
谭延闿出走后,林支宇由警务处长而升任临时省长。林虽位居省长,并不能参与赵恒惕的机密。他对赵唯命是从,而赵则大权在握,俨然是个太上省长,重大的省政措施都要秉其意旨办事。林不敢独断专行。例如,我之出任长沙市政公所总理,就不是由林省长决定,而是由赵总司令指派的。十二月初某天,赵恒惕托胡典武来向我致意,说石醉六请辞长沙市政厅长,拟将市政厅改为市政公所,要我担任市政公所总理。我因为赵刚刚上台不久,时局还在动荡中,推辞不愿担任,胡典武说:“赵炎公(赵恒惕号炎午)认为市政建设很重要,你在外国的时间久,见识多,出长市政,最为适宜,一定要请你帮忙。”赵恒惕和我见面时,也是这样表示。经他再三敦促,我自己考虑到借此可以在家乡做一番事业,而孙科当时也正担任广州市长,因此答应下来了。其时,市政公所每月仅有经费五千元,还不能按时领到,要拿财政厅的拨条到省河厘金局去抵借。可是,在赵恒惕的本意,却是以此为酬庸工具,来报答我帮助他赶走了谭延闿。谭延闿则因此对我怀恨甚深。一九二八年安徽省政府改组时,蔡元培、孙科等在南京行政院会议上联名提出我为省府委员兼建设厅长。谭延闿时任行政院长,他坚持不同意,结果没有通过。会后,蔡元培派车接我去大学院谈话,他劈头就问:“你和组安先生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我说“别的没有,只是民国九年在长沙赶走了他。”蔡先生连说:“难怪,难怪!”接着,他把开会的情况告诉了我,并叫我不要介意。
(二)
一九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深夜,长沙城里发生了一次重要的流血事件。被害的人多是湘军现役军官,计有六区司令李仲麟、二旅四团团长瞿维臧、第一师司令部执法官萧泽源、二旅四团团附曹广遂、前湖南政务厅长易象、烟酒专卖局局长张自雄、湖田局局长叶隆柯等人。这是一次经过缜密布置的有计划的大屠杀,惨遭牺牲的大多是拥程倒谭的人物。
这天上午,我在通泰西街私宅为回湘省亲的林镜南(长沙人,时任北京政府陆军部军衡司长)设宴洗尘,并邀彭允彝、李醉吾、杨丙和严幼甫等人作陪。李仲麟也在被邀请之列。别人都来了,他却没有到,听说回长沙金井乡间李家祠堂挂匾去了(李仲麟是农民家庭出身,青年从军,超升很快。当了司令以后,乡下人都对他另眼相看。宗族间对他更是捧得很高。李在倒谭之后,动了“衣锦还乡”的念头,趁“冬至”回乡祀祖,到祠堂上匾。他的字学黄山谷,写得甚好,也学做诗,俨然儒将风流,恭维他的人很多。因此,更助长了“踌蹰满志”的情绪,平日麻痹大意,以为赵恒惕对他莫可奈何)。
当天晚上,我试打了一次电话到六区办事处询问,李仲麟自己接电话,说他下午刚进城,没有来陪客。我问他那里有人客没有,他说只有周介祹(新任警务处长)在,没有外人,要我和幼甫去谈谈。我邀幼甫同去,刚走到泰安里口叶开鑫住宅前面,卫兵问“口令”,我们回答了;再问“特别口令”,我们答的不对。卫兵正要阻拦,幼甫情急智生,说“我们是来会叶太太的。”到了叶家一问,才知道是临时换了口令。我由叶家回到自己家里,已是十一点多钟了,想到情况有变化,要给朋友打个招呼,于是再打电话找李仲麟。我在电话中说“季隽兄,我们本来是来看你的,临时到叶家去了一趟,不来看你了。今晚换了特别口令,你要注意些!”他大意地回答说“这有什么关系,怕什么!”
这天深夜五点多钟的时候(十二月二十五日黎明以前),我在睡梦中被电话铃声惊醒,有人在电话中告诉我:李仲麟被杀死了(这个电话究竟是谁打来的,我至今还猜度不出)。清早起床后,我家的厨工进来对我说:他上街去买菜,被门口站的带红布条子的枪兵拦阻住,不准通行。过后不久,哨兵就撤走了,街上没有动静。早饭前,刘重(号谦实,资兴人,旧国会议员)匆匆跑来,说在北正街碰见刘重威(邵阳人,当时在赵部任营长。一九二六年任第三师旅长,被唐生智在衡阳处决)骑马招摇过市,厉声地问他“你在外面跑什么!”刘重胆小怕事,通过我和连士清(在美领事馆任翻译)的关系,躲进了福屋门外的美国领事馆。随后又有人来告,李仲麟被杀后,头被割下来挂在多福寺(今解放路柑子园口)门口电线杆上示众,他的妻子则抱着无头尸身痛哭不止。
我听到良友惨死,为之忧心忡忡。随即打电话给夏斗寅,请他来我家一谈。夏来到以后,我问他知不知道李仲麟被杀的事,他说“早已知道了,死了七八个,不止李秀隽一人。”他接着说,赵恒惕昨夜在他那里待了大半夜,到天亮时才回司令部去。我邀他同去见赵恒惕,他答应了。当我们走进湘军总部赵的办公室时,只有总部参谋长唐义彬、秘书长钟伯毅和首斌在座,赵恒惕靠着一张椅子在烤火,神情恍怫,默然无言。我问他“昨夜死了这么多的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郑重其事地辩白说:“我只圈了李仲麟一个人!”我说“李仲麟的脑壳挂在多福寺门口示众,省会之地,观瞻所系,这不大好!”他听了我的话,对夏斗寅说“霖炳(夏斗寅别号),你去负责收殓一下。”随手批了一张发洋五百元的条子交给夏斗寅。李仲麟被害后,就是由他照料收殓的。事后听人家说,张辉瓒拟出的黑名单上多至四五十人,我和幼甫的名字都列在其中,而没有杨丙(可能因为他们是日本士官同学)。这次屠杀,是赵恒惕根据张辉瓒拟的黑名单圈定后,交叶开鑫执行,直接指挥杀李仲麟的,为营长赵茂林,其人与李有宿怨。叶开鑫事后对幼甫说过,那次杀李仲麟等,他事前并不知道,当时奉命随即执行。可见赵恒惕对我说他只圈了李仲麟,显然是白昼撒谎,欲盖弥彰!总之,在谭派死党张辉瓒看来,这些人是拥程倒谭的罪魁祸首,势在必去;在赵恒惕眼中,李仲麟等飞扬跋扈,终是心腹之患,因此,刚刚上台一个月,就认友为敌,悍然伸出了血手。
李仲麟之死,固然是赵恒惕、张辉瓒等人蓄谋已久的有计划的屠戮(据传事机极密,连身居临时省长的林支宇也未预闻);但他自己的麻痹大意,丧失政治警惕性,也是致死之由。记得一九三○年冬在上海时,李午云(平江人)对我谈过:一九二○年他在六区司令部担任参议,李仲麟回金井宗祠挂匾,他适在长沙,听到外间谣传赵恒惕将不利于李,便赶往乡间通风报信。李在半路上遇见李仲麟坐轿子进城,告以外间风声很紧,劝他莫进城去,速由榔梨、渌口绕道回醴陵,免遭毒手。李仲麟却毫不在意地说:“赵炎午现在不敢动我的,他还在拉拢我,答应将我们的部队编师哩!”谁知“世路风波险”,就在这天深夜,李仲麟竟成了赵恒惕的刀下鬼。
十二月二十五日,赵恒惕以湘军总司令名义宣布李仲麟等罪状,说李仲麟、瞿维臧等谋乱有据,拿获正法。廖家栋于惨案发生后出走武汉,第二旅旅部及所属第四团均被解散,叶开鑫升任二旅旅长兼省会戒严司令,他的安民布告也随即贴满街头了。至于李仲麟的部队,则被张辉瓒等就地解散。一九二一年,程颂公追念死者,作过一首《悼七士》的五言古诗:“愚者多嫉妒,庸人每残贼;忠义匪所存,利害易为惑。吾党盛秀士,夙志剪荆棘;奋起乡闾间,行义如不克。一时殉权者,岂不借其力;宵游方从容,晨起已锄殛。始知争逐际,祸福未可测。哀哉二三子,含冤痛沉抑!”有感而发,情见乎词,是那个仕途黑暗、朋党倾轧的旧社会的真实写照。
关于易象临难时写的绝命诗,仇鳌先生记的是“天外飞来事可惊,丹心一片付浮沈。救乡救国终成梦,留取他生一恨吟!”姚文发表于《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辑的是:“天外飞来事可惊,丹心一片付浮沈。爱乡爱国都成梦,留得来生著憾林!”刊诸湖南《文史资料》第三辑时,其结句是:“□□□□未了因”。据我回忆,三者都有出入。这首当年传诵一时的绝命诗,原文是这样的:
天外飞来事可惊,丹心一片付浮沉。
爱乡爱国终成梦,留此来生一恨吟!
易象遇难后,程颂公致送遗属光洋一千元。他的次妻(易的元配是田汉同志的舅母,现在年近九十,住北京)辛景林,为纪念丈夫殉难,在长沙李文玉金号打了一块带链子的金牌,随身佩带,牌子上就刻着这首诗。后来,辛景林曾将这块金牌拿给我们夫妇看过,故印象最深,至今犹能记及。易象号枚臣,长沙人。一九一五年秋,蔡松坡密谋起兵讨袁,我奉先君之命由美国回到日本,有所策划。其时,易正亡命东京,我们初次订交。后来他在上海办晚报,又常来往。一九二○年被害前不久,程子楷告诉我说他来了,住在落棚桥某亲戚家。我曾去看过他一次,匆促间未及深谈,不料竟成永诀。